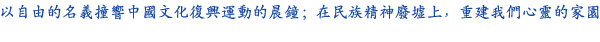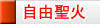[貝嶺:美國加州大學(爾灣)翻譯和文學寫作國際中心理事會執行理事]
作者按︰此文原為答日夲文學刊物《藍》主編問。書面回答始於2005年10月(巴黎)、11月(西班牙南部海邊Mojacar FUNDACION VILPARAISO駐地)。2007年11月改定於美國波士頓。
關鍵詞:流亡
流亡中必要、非要面對的是「孤獨」。是大量以「孤」開頭的形容詞:孤獨、孤單、孤立、孤寂、孤零零、孤伶伶(自憐嗎?)、孤立無援、孤形吊影、孤掌難鳴、孤家寡人(假如你「不幸」單身、沒有家庭)、孤陋寡聞(那時還不是網絡時代)、孤魂野鬼(在外語的大原野)……它們變成了代替你的名詞,甚至成為如影隨形的動詞。你還不能被這「大原野」埋了(多少流亡作家埋沒了,母語丟了,又沒有真在這「大原野」上疾走)。在這「大原野」上,你還必須有些「孤高自許」(動詞意義上,甚至阿Q意義上的)。你要孤注一擲,向內,也向外,坎坎坷坷,跌跌撞撞,視若無睹,即使「鼻青臉腫」,也要試著,在這外語的「大原野」上行走。
一.
問:你如何命名或定義1989後中國的流亡文學、流亡作家?何謂中國流亡文學的精神和流亡美學?
答:確切的稱謂應是:流亡的中國文學和流亡的中國作家。
(另一個聲音告訴我:虛妄啊,大得讓人生畏的虛妄。)
1989年「六四」事件,中國發生了因殘酷的武力殺戳導致的民眾死亡和隨之的全國性政治「清洗」。部份的中國作家、知識份子滯留或逃往海外,在歐美、日夲定居或漂泊。在這一特定的政治和時空背景下,產生了帶有流亡色彩的文學作品和作家群。流亡的中國文學也包括身居祖國、文學作品卻只能在地下流傳或國外發表或出版的作家作品。在這一流亡文學背景下的作家、文學知識份子,介於20至30位之間。而受到此一背景影響的在歐美、日夲的(中國、臺灣、香港)學者、科學工作者、藝術家、留學生及新移民,人數應逾數十萬,其中包括了更多的作家、知識份子。
數字,代表著流亡文學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必需的文化和精神氛圍。故,我曾將1989年後流亡的中國作家和流亡的中國文學稱之為二十世紀最後一波流亡作家潮和流亡文學現象。
然而,無可回避的是,大部份流亡作家因背井離鄉、喪失母語環境、語言不通,或轉入移民社會的大眾文化領域,或在異域為「稻糧謀」。部份流亡作家投入了政治反對運動,全心轉向對祖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現狀的分析批判。
逾十五年來,流亡的中國文學沒有形成輝煌的群體,也未能產生足夠數量的偉大文學作品。近十多年來,很多文人、作家中止了流離失所或異域暗淡乏味的僑民生涯,回到中國,甚至被吸納到商業浪潮或大學的教授體制內。這也無可厚非,如果回得去,回「家」或者探「親」難道有錯嗎?他們絕不是上世紀50年代那些帶著可愛(也可怕)的天真或浪漫情懷回去擁抱社會主義祖國的一代人。我這一代的他們,帶著無比複雜、已不可能被再馴化的頭腦和完全異質化的經歷回去,他們和那個更大的「大眾」社會油水交彙,異化和被異化,己激盪出全新的「火花」。
流亡文學的精神和流亡的美學是在二十世紀流亡文學的歷史和傳統中漸漸確立和產生的。它包括從祖國及民族歷史、從個人的歷史中沉澱出來的記憶和反省,這一切,因異域的流亡經驗深化,獲得新的視野。
然而,喪失就是喪失,就是現實。除非你的作品被儘快譯成其他語言出版(包括用繁體字出版),或至少,在僑民社區用母語出版(會有人讀嗎?)。祖國,即使讓人魂牽夢繫,仍將愈為抽象,成為流亡文學和流亡作家的背景,讓位於語言/母語,讓位於回憶,那構成流亡文學存在的唯二依託。
(多沉重的闡述!)
流亡並非一無是處,它給予全新的視野。記得有著流亡經歷的偉大知識份子薩依德(Edward W. Said)描述過,流亡,賦予流亡作家甪雙重的視角(Double perspectives)看待世事和過去。眼前的情景和母國的情景、新的觀念和經歷對照著以往的觀念和經歷,它們並置並撞擊,產生新的、難以歸類的思想和作品。
流亡的現實:最好的現實(唐吉訶德式的現實)是,最終(何時是最終?),一個流亡作家成為國際文學共和國中當之無愧的一員,一位真正戰勝了語言和文字障礙的世界公民。
詹姆斯‧喬依斯說:流亡就是我的美學。流亡,對我還意味著︰痛定思痛,置死地而後生。
問:詩人孟浪在〈必要的喪失-----1989後的中國流亡文學〉*1一文中說:『1996年以後流亡文學的形態和陣營由於相互之間的某種陌生感、疏離感、甚至排斥感。開始直接面對來自中國體制內或「遊刃」於體制內外的中國大陸作家。』
答:確實如此。
人類的天性如此。流亡作家之間,流亡文學、流亡作家和政治、和反對運動、和中國國內文學市場及文學環境,甚至和國內作家、知識界的分化狀況,均有著複雜糾纏的關係。這不是特例,二十世紀歷史中的納粹德國時代、法國貝當時期、西班牙佛朗哥統治時代、前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時代(哈維爾曾告訴我的)、拉丁美洲各國的軍人獨裁時期、(納丁‧戈迪默*2向我描述的)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索因卡*3和我談到的)奈及利亞(尼曰利亞)軍政府獨裁時期,乃至今天古巴、越南、緬甸、伊拉克、伊朗的流亡作家及流亡文學歷史,都曾歷過類似的情形。
問:流亡詩人黃翔在〈流亡遊戲――質疑所謂「反對派」並對「異議者」持異議〉*4一文中曾嚴正痛斥『以流亡的名義戲耍人生者,遊刃於海內外,吃盡東西方的好處,稱之為文化政客……。』他認為,流亡者中有真流亡者和准流亡者或真流亡者和假流亡者之分。
答:我無法臆測黃翔在文中反覆剖析並予以抨擊的以上各類人物和「異議者」確切指誰?但從他此文發表的時間點(當時在美國的中國流亡者正在為一位高壽卻身患癌症的政治流亡者劉賓雁先生舉辦祝壽活動),我大概知道他此文寫作的直接所指。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文對當代中國政治和文化中一些從官方到反對運動都習以為常的一些現象和積習的敏感審視和批判,他的質疑不僅尖銳,而且重要。黃翔觸動了一個敏感的話題和歷史中敏感的部份。接下來,需要其他思考者和他一起,在這一命題上繼續予以細緻的梳理及更多的闡述,包括對歷史中人物的審視。當然,這需要一些勇氣,不是大到視死如歸的勇氣,而是不怕犯「眾怒」,直面自身歷史的勇氣。
但是,我不認為流亡中一定還要區分出「真流亡」和「假流亡」,流亡就是流亡,假的就不是流亡。每個流亡者的流亡背景、流亡原因和流亡理由不會相同,流亡者中每個人的信仰、政治見解、政治立場也必有不同。甚至,流亡者對流亡的態度也有差異。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嗎?不是,它是一個既得利益者和權勢者集團。現在的中國政府是馬克思主義者政府嗎?也不是,它是一個由既得利益者和權勢者集團中的實用主義者和技術官僚組成的專制政府),或一位曾在官方文壇紅極一時的作家,並不必然就不被「禮送」出境或不選擇流亡。只要你在特定的時刻或因特別的原因不被黨、政府、以及所屬的國家機器所容忍,只要你「惹」了它或公開表示了重大的異議,只要你曾被拒絕入境祖國、或者,你被要求接受某些「條件」才能回到祖國。甚至,僅僅因為恐懼,或對自由的嚮往, 你都可能被迫流亡或選擇自我流亡 。
是的,「流亡」是個有著無限包容量的龐大概念,並已被世人濫用。流亡不是兒戲。流亡首先是一種不幸的境遇,如不予以轉化,甚至可以摧毀人的精神,使其喪志。
上一世紀末的中國流亡者中,主動的、想方設法要離開中國的人是絕大多數,只有極少數人是被迫流亡或被中國政府「遣送出境」的。除了作家的流亡,政治流亡者構成了中國「流亡者」中的主體。流亡者對自身的反省,對「流亡」夲身的質疑,在這一命題和這一現象下所發展出來的思考,將極大豐富後人對流亡中的歷史事件和流亡中人複雜性格的探索。
二.
問:記得1989年「六四」以後,你們醞釀成立『中國流亡作家聯盟』,並且創辦刊名為《流亡》的流亡文學雜誌,為什麼後來改名《傾向》?你在《傾向》停刊後所發起和創辦的中國獨立作家筆會是否具有「流亡作家筆會」性質?
答:1989年「六四」之後,確實有一位在美國的中國詩人菲野曾在三藩市醞釀並公告成立中國流亡作家聯盟,但成立的過程匆忙。在那一時刻,他曾請我幫助聯絡一些剛剛離開中國,或滯留歐美的中國詩人、作家共襄此舉。那時,我代他問了一些詩人、作家,有人電話應允、有人後又否認,甚至懷疑企圖。
文人的天性如此。
重要的是,過於粗糙,應允的沒有簽名或信件,有些人沒有被問到,名字也上了新聞報道。主事者沒有去做充分的溝通和協商,缺了文學團體中最基夲的簽名認可要素。
最終,中國流亡作家聯盟消失了。我曾在〈筆會誕生始末〉*5一文中寫到:
「1989年底,曾有旅美詩人菲野籌劃過「中國流亡作家聯盟」,想把以上不同歷史背景的作家以流亡作爲共同點聚合在一起。但由於過程的匆忙、粗糙乃至多疑和私心,此一努力失敗了。為此,還造成了部分作家長久互不往來的結果。」
然而,它雖失敗,但在那樣一個時刻,它的出現和宣告有它的時空和歷史召喚,在那時的世人心目中,也是宣告,是中國作家在那一時刻應有的聯合,也是部份走上不歸之途的中國作家發出的良知聲音。
當然,那隨著「六四」而來的流亡太輝煌,在世界的注目聚焦下,也太戲劇化,狂妄和蠢動的「雄心」也太多。
那時,我尚未做好應付流亡生涯中艱難面的心理準備,也缺乏一個藉藉無名者在「流亡」時的痛切體驗。
確實,在當時(1990年前後)的美國,也有流亡中的友人試圖創辦以《流亡》為名或其他刊名的流亡文學雜誌,那也並非由我發起或主事,可我堅決支持。可惜,主持者和編輯者當時均無從瞭解,這樣一份刊物的創辦是要以破釜沉舟的奉獻和時間精力的大量付出為前提的,不可以自以為有一筆筆送上來的創刋經費,還有一份薪水能讓人邊維生邊創刋的。何況,還有來自同一陣營中的詆毀和暗箭。所以,最終無以為繼,刊物未出己先失敗了。
嚴格上講,1993年創刊的《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和之前夭折的中國流亡作家聯盟和《流亡》文學雜誌沒有任何必然的傳承或銜接。但是,在流亡的美學和流亡的象徵上,無疑,有其精神傳承。
問:《傾向》是我看到的中文刊物中最有心為歷史留証的。其中『放逐中的寫作專輯』【第6期】『當代中國地下文學專輯』【第9期】以及每期都有的『中國大陸非官方文學刊物一覽表』、『中國文學藝術及作家藝術家備忘錄』等,是見証,具有相當的史料性。
答:那也是《傾向》創刊的目的之一。數十年來,那些地下文學作品,十多年來,那些在中國地下出版的文學刊物、畫刊和書籍,都處在自生自滅狀態。編輯『中國大陸非官方文學刊物一覽表』是為了呈現地下文學的歷史演進,編輯『中國文學藝術及作家藝術家備忘錄』是為歷史存擋、作証。是為地下文學中人的我,是《傾向》編輯同仁們應有的責任。而刊發流亡文學和地下文學作品,甚至以專輯呈現,也是《傾向》的使命。
問:《傾向》的理念可以理解為是「流亡中的理想主義信念」嗎?
答:觸到了本質的表述。因為有些價值必需守護和凸現。《傾向》的產生源於流亡以及上世紀80年代中國地下文化中滋生的堅持和信念,一種迫切感和責任感,帶著青春期最後的熱情。無疑,它是理想主義的。而且,我不否認《傾向》是帶著政治性的。十年前,在經濟剛起飛的專制中國,舊的意識形態瓦解了,錢在消解一切,社會正面臨全方位商業化的巨大變遷。在早期共產主義中國,毛澤東思想和共產黨教條對人的洗腦和控制、人與人之間相互的監視,已轉化為用物質和錢左右人的思想和行為、用大眾文化和通俗娛樂來培養人的趣味和審美、用龐大的國家警察機制監視、恐嚇可能的反抗者和異議者。怎樣認識政治專制和商業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新型社會和文化形態?在政治專制和商業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社會和文化形態下,異議的美學、反抗的文化、地下文學的精神和價值怎樣呈現?那時,確實有著緊迫感。
《傾向》不是一份純文學刊物,那類刊物在中國、台灣和香港都不缺,甚至己太多了。《傾向》不是,至少不只是一份流亡的文學刊物。《傾向》直面中國的現狀,試圖從文學和思想上介入,我們盡了全力,雖然不自量力。1996年在北京,我甚至直接前往國家新聞出版署申請《傾向》的注冊,要求在中國公開出版發行。當然,《傾向》不可能被允許在中國出版和發行,只能在香港和台灣印行(1000至2000夲不等),但通過寄贈和攜帶,刊物抵達了中國,到了寄贈者或寄贈圖書館手中。
2001年,《傾向》停刊,部份原因是由於2000年夏秋我在北京因印刷出版了第13期(那不吉利的數字)導致的被捕入獄,刊物沒有錢,編輯群也因我的入獄而在中國停止了後續的編輯工作。2001年至2002年,由於籌創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我編了一半的《傾向》第十四期被迫擱置,然後,又因更迫切的責任,我必須投入翻譯、編輯、出版哈維爾*6六部著作及一部國際知識份子和作家評論和研究哈維爾的文選的工作。《傾向》再被擱置,竟一置多年。當然,《傾向》的另一延伸,傾向出版社因哈維爾著作的出版而在台灣創辦,但《傾向》雜誌和傾向出版社畢竟不同。
是的,《傾向》沒能繼續出版和創辦獨立筆會在時間上重迭了,但不是必然的關係。人的精力畢竟有限,不可能心想事成。創辦獨立筆會曾是更大的召喚,是我2000年秋被營救出獄後不可推脫的責任。正如蘇珊.桑塔格在信中對我所說:「但你別無選擇,對嗎?」*7
在〈筆會誕生始末〉一文中,我對那段歷史曾予以回憶:
「2000年11月,我應邀赴洛杉磯接受美國西部筆會中心頒發的2000年「自由寫作獎」。國際筆會主席霍梅羅‧阿瑞底斯*8(Hemero Aridjis, 墨西哥詩人)專程前來參加美國西部筆會的文學獎頒獎儀式,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代表國際筆會和我探討能否創設一個(不同於官方的中國筆會)符合國際筆會章程的中國流亡作家筆會。在那幾天,霍梅羅‧阿瑞底斯、美國西部筆會中心的多位理事均在和我商討關於籌組此一中國作家筆會的可能性。他們認為,我及其它中國作家在中國的遭遇說明,國際筆會中需要一個能夠真正關注作家人身自由、創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中國作家組織。
…………
洛杉磯之行之後,我為此事陷入思考。我從未加入過任何作家組織,成年後,也沒加入過任何政治組織或團體,不參加任何組織或團體,已成為我的人生信條。此刻,要我來籌創一個作家筆會,有違我的行為準則,這使我十分為難。
但是,任何一位作家或文字工作者,特別是用中文寫作的作家,假如因為文字、因為文學,因為爭取或踐行出版自由、表達自由而受到審查、迫害,甚至被捕入獄,我,作為文學同行,特別是作為中文寫作的同行(不管彼此的私人關係好壞或政治見解是否異同),不應沈默、無動於衷,更不應幸災樂禍。或者,只是等著、看著西方的文學同行,西方的作家組織表示公開的呼籲或抗議,等著、看著西方的政府去努力營救,那不正常,也令人蒙羞。假如我們有一個自己的作家組織(它是作家的精神共同體),平時,它對作家不具任何約束力,因為沒有什麼比自由和個人性對作家更重要了。可一旦發生了作家的作品受到審查、被禁,甚至作家本人受到迫害的事件,不管它來自哪個國度,除了每個作家個人的抗議聲音,我們還有一個作家的組織可以發聲,可以運作,特別是通過與國際筆會、各國筆會及其它人權組織的合作,去營救,聲援,並為作家的避難、生存和寫作提供幫助。這就值得我出來籌創這一筆會,也是這一筆會的真正價值所在。1990年代,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拉什迪)*9的遭遇,這世界上其他許多作家的遭遇,2000年我的親身經歷,在在都給我上了這一課。
若這一筆會能夠接納他們成為會員、甚至有一天,這一筆會是以這些作家為主體,筆會的創設才有必要性和緊迫性。而真正理想的作家團體,應該僅僅是作家的精神共同體,一個自由的文學共和國。
我的親身經歷已使我不能不去重新思考。在兩難之時,我首先獲得孟浪的支持,並開始和海內外的作家友人們商談,也獲得了鼓勵與贊同。
2001年初,我告知國際筆會,我願意嘗試去推動創設獨立的(中國)作家筆會,我表示,讓我試一試。隨後,多年來和我一起編《傾向》雜誌,也是我入獄後,在美國為我呼救聯絡的孟浪和我開始分別與在海外的流亡作家們、與在中國的異議作家,為成立筆會的事,進行了溝通和討論。我和孟浪當時的共識是,只有在獲得了中國國內的,不依附於官方體制的獨立作家們的支持,才值得去設法籌創這一筆會。
2001年四月前後,我與孟浪開始一個個致電邀請旅居海外的作家、流亡作家、中國國內的作家參加筆會。
筆會的會員包括了流亡歐美的作家、知識分子、記者以及中國的作家和文化人。
按照國際筆會的慣例,一個新成立的筆會,它的會員應該至少有二十位以上,並能獲得國際筆會的特別關注。同時,還須向國際筆會提出申請成為國際筆會分會的書面請求,並獲得國際筆會等待批准的回覆認可。而最早的分會會員還需獲得國際筆會的審核。他們的履歷和著作均需有英文的譯文及說明,國際筆會才能去審核。待每一個會員的資格均已獲准,並經國際筆會認可,此一筆會才可能被列入未來的國際筆會年會的入會討論議程。
筆會的中文名稱,曾經在部份創會會員中有著多次討論,並且要考慮到怎樣和英文譯名相符,「獨立」兩字是由萬之向我提議,其他會員也提出了不同的名稱建議,筆會的英文譯文名稱「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也是我在和部份會員及國際筆會的多次探討中最後確定的,我們曾研議過使用例如自由(FREEDOM)作家筆會等不同中文名稱,但均不理想,也不易讓英語讀者理解。經國際筆會總部和我的諸多溝通和認同後,才決定採用「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一名。
這些具體工作要耗費精力和時間,因為在中文作家普遍不瞭解國際筆會的運作、不瞭解國際筆會憲章,不知為何要創辦一個筆會的情形下,和一個個居住在世界不同地區,個性差異和時差同樣巨大的華人作家們溝通,並要勸動、說服每一個人認同,要日夜顛倒地投入。那時的孟浪和我,有時日以繼夜,十幾乃至上百小時,自付的電話費昂貴,因為要寒暄、要談各自的近況,還要談天說地,然後才能切入正題。這常常還不保證每個作家願意加入。因為作家們,尤其是厭惡並且從未加入過中國官方作協的作家們,並不都認為需要這樣一個組織。
作家友人們有著許許多多的建議,不管他們願不願意參加這個筆會,他們的善意和理解,在在鼓勵了我們。他們對我的忠告,悲觀的預言,彼此的成見,也使人心情沮喪。
終於,這一切都熬過來了。
2001年10月,作為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的籌創人,我被國際筆會邀請列席11月底在英國倫敦舉行的國際筆會年會,以觀察員身份全程列席年會,因為我負有爭取本筆會在年會上被接納為國際筆會分會的責任(這責任有點太大了),我必須在正式會議之外的所有休息時間向前來參加年會的80多個分會的代表介紹本筆會,並遊說他們支持本筆會加入國際筆會,這是一份艱巨的工作。
遺憾的是,中國筆會(中國作家協會)在此次國際筆會年會上再次缺席。來自台灣的中華民國筆會代表和海外華人作家筆會的代表也未興會。
終於,在倫敦國際筆會年會的全體代表會議上,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加入國際筆會案被列入議程。在美國筆會中心的支持下,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可能是全世界人數最少的筆會)是由全世界最大的筆會美國筆會(有逾五千名會員)提名,推薦成為國際筆會新的分會。美國筆會自由寫作國際項目主任、美國筆會代表Larry Siems代表美國筆會作了精彩的提名發言,隨後,國際筆會主席要我作為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籌創人,向各筆會代表用英語(我的破英語)作本筆會成立原因及申請加入國際筆會理由的發言演說。我首先對中國筆會(中國作家協會)的代表未能與會表示真心的遺憾,我說,我感到孤單和遺憾,我期待在這裏和中國筆會的代表握手、交談,直言不諱地各陳己見和交換文學信息。我說,我手上還帶來了一些在中國失去消息或被捕入獄作家的資料,要轉交中國筆會代表,請中國筆會代為瞭解一下這些作家的近況及能去探望一下在獄中的作家。我當時還出了一個糗,我說,我若真能和官方的中國筆會代表在倫敦見面,應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可我不會用英文講這一諺語,現場的代表見我舌結口拙,連比帶劃,意會後大笑。
正題,我主要談了三點:
1. 文學和作家在中國的處境。流亡作家和中文的流亡文學。
2. 我們筆會成立的背景、原因和歷史責任。
3. 怎樣看待和怎樣面對中國的最大的官方作家組織,中國作家協會及它的另一塊牌子中國筆會。我的大意是,我們並不代表國家,我們希望代表的是作家和文學的尊嚴和自由。我們並不是為了對抗他們而來的,中國獨立作家筆會是為了維護和爭取出版自由和表達自由,為了作家個人的尊嚴不被侵犯和侮辱,為了文學而成立的。正是因為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筆會)不敢爭取和維護作家的出版自由和創作自由,甚至對在中國不斷發生的傷害作家尊嚴和自由的事件視而不見,才使我們這一筆會的創立有了必要性和緊迫性。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和中國筆會(中國作家協會)的關係應該是平等互動、相互監督並督促彼此真正遵照國際筆會憲章,維護作家、文學的尊嚴和自由的關係。
我的發言竟也獲得了幾乎所有與會代表的持久掌聲,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的申請加入,是整個年會的高潮,也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許多筆會的代表紛紛走上來和我握手致意,並在隨後的發言中強調,國際筆會等待我們的加入,已經等了十多年。終於,我們可以坐在一起了。
多個流亡作家筆會,如古巴、伊朗、越南流亡作家的筆會代表給了我擁抱。
我的發言之後,各分會代表曾有過熱烈的爭論及討論。在中國筆會(中國作家協會的另一塊牌子)缺席的情形下,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的加入先後受到了三個國家筆會代表不同的提問和質疑,他們是巴勒斯坦筆會、法國筆會和日本筆會,日本筆會代表對於我們筆會為什麼要稱為「獨立」(Independent)表示不解,質疑這一概念是否會讓人有獨立於中國的聯想。法國筆會代表質詢了我們筆會會否與中國筆會發生衝突,以及我們的筆會有多大代表性等問題。而巴勒斯坦筆會代表則認為中國筆會一貫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爭取獨立和民族生存的權利,我們這一筆會的加入是否多此一舉等。我對此一一作瞭解釋和回答,我強調:
1.「Independent」是指作家個人立場和政治見解的獨立性,而非指國家的獨立。
2.我們筆會不純然是一個流亡作家的團體,它也包括了在中國境內的作家、香港和海外華人世界的作家。
3.我們無意取代任何其他的筆會,我們無意代表國家,反而希望和所有的筆會,特別是中國筆會、海外的華人筆會建立起建設性的對話和互動關係。
此一解釋及陳述,也獲得了其他分會代表的鼓掌和發言支持。巴勒斯坦筆會代表在會後還向我致歉,表示他們私下會支持,他們公開的發言主要是為了不惹惱缺席的中國筆會。而日本筆會則在會後表示理解和支持我關於本筆會爭取出版自由和捍衛創作自由的表述。
最後,投票表決,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加入國際筆會案獲得超過八十個筆會代表的支持,他們對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的加入投了贊成票。只有巴勒斯坦筆會和法國筆會投了棄權票,沒有反對票。」
回頭來看,在那一時間點,即使創辦不成,成笑柄,我終會一試,以不辱使命和信任。在那一時間點,也幸虧有孟浪和我一起來做,相互鞭策。
可是,我越來越清楚,我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傢夥,天性也不適任何團體。
《傾向》停刊於2001年,新世紀之初。
當時,我已身心俱疲。在海外辦《傾向》的艱辛,是外人無法想像的,若沒有稿費,對不起作者,而編務、發行、一應的雜務也需多人分擔。即使出版了,若放在書店賣不出去(我拒絕過期刋物被打成紙漿),最後,連存放《傾向》的倉庫都要東求西借、東挪西移。
因為沒有錢寄贈,多少年來,我都是利用國際航班幾十公斤行李的托運上限,肩背身扛,帶著它發行。我也常求人乘飛機時帶一點,最後,都成為條件反射了,令友人避之不及。所以,夲想過一兩年再復刊,最後,竟一拖,停到今天。
何況,《傾向》(精神的「毒品」嗎?)讓國家動用龐大警力,查抄、沒收、恐嚇、抓人入獄、搜查印刷廠、罰钜款。最後,要驚動國際文學界,驚動美國政府,要國務卿介入,要由錢其琛發話,要以「遣送出境」,要流亡,我才能出獄。文學需要國家如此「興師問罪」嗎?
是的,在這百年難遇的新舊世紀之交,我這「禍害」被驅出國門了。是的,《傾向》遭國家一擊,幾乎垮了,國家好像贏了,國家真的贏了嗎?《傾向》失敗了,可《傾向》難道不是雖敗猶榮嗎?
可想來,我人出獄了,《傾向》卻停了,真對不起救我出獄的人。
所以,一直想著再復刊。而且,我也在籌劃著未來的復刊之事,新的《傾向》將延續老《傾向》的創刊精神,但將轉型成一份國際性的文學、思想和藝術刊物,甚至是一份中英文雙語刊物,英文部份除了中譯英的作品,也將刊發國際作家、知識份子的英文作品、文論和訪談。一年出版兩期,每期頁數仍逾三百頁。而且,將恢復稿酬。
(未完待續)

1, 貝嶺(1999年9月)在哈維爾總统辦公室

2,貝嶺(2003 年 11月) 和戈蒂瑪在墨西哥城她的房间間內交談
(娜汀 ‧ 葛蒂瑪(Nadine Gordimer 1923---- )南非小說家,199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3, 貝嶺(2002年 2月)在台北國際藝術村和索因卡
(渥雷.索因卡( Wole Soyinka 1934 ---- )奈及利亞詩人、劇作家、小說家、評論家,也是非洲民族的自由鬥士和政治領袖。由於「以廣闊的文化視野創作了富有詩意的人生戲劇」而獲得 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非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