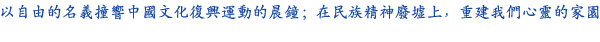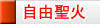十年前,一個從未被世人認可的地下詩人,由於某種機遇,更確切的說,是因為某種宿命,來到了一個可以無需恐懼地自由表達,但也可能無人聆聽的西方世界,暫時,甚至長久的中止自己的寫作〈詩、小說或者散文、劇本〉,去為他所經歷的曾遭遮蔽的文學歷史中的個人、作品和不幸的存在狀況去代言和申說,甚至奔走呼號,這也許並不是一個明智之舉,本應有更為傑出的文學同行比我更適合站在這一位置上談論中國歷史中的地下文學和地下文化,但是,這一情形並未出現,中國的文學歷史中沒有出現如俄羅斯地下詩歌中,如布羅茨基()那樣的形象和角色,也缺乏如索爾仁尼琴()那樣擔當歷史見證的偉大文學良心。原因不是其他,僅僅是因為中國當代歷史中暴政的殘酷和身為其中一員的我們自身的不察,更可能的是,二十世紀下半叶中國地下文學歷史中最優秀的個人大都被暴政從肉體上消滅了,或者,從精神上擊潰了,以致於十年前,暫時,只有我這樣的相對孱弱者和倖存者來擔當這一使命。而今天,濟濟一堂、登上講壇的各位中,已有更多的强悍之人,已擔當這一使命。
大約在十多年前的北京,在我們那部份文學的歷史中,曾經有位先行者〈或「奇人」〉永遠離開了人世,他走的時候沒有喧嘩,甚至沒有驚動鷹犬般明察秋毫的國家警察。他的名字叫趙一凡,我之所以稱他為「奇人」,不只是他有著沉靜的、幾乎不可能捕捉出年輪的神態,更因為他是地下文學歷史中的見證人、主要的資料收藏者和贊助者。可以確信,除了國家的『警犬』---國家安全局和公安局,沒有人會像他那樣數十年來收藏、保存了如此多的地下文化資料,特別是地下文學的原始資料。他是七十年代初紅色恐怖環境下北京最早的地下文化沙龍主辦人,他也是一個傑出的語言學家。他幾乎未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卻在十三歲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他可能是中國最古老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內最博學的幾個校對之一,當代中國使用率最高的幾部中文字典都是由他校對和審核後流於世的。我始終記得他那異於常人的相貌———巨大的頭顱〈那真是奇人異相〉支撐在極厚的雙肩及胸膛上。他的額頭極寬,明淨而泛光,他是一個下半身癱瘓的殘疾人。他一生中絕大部分的時間是坐在椅子上工作或閱讀,當你去探望他時,他從埋首工作的桌子上伸出他那巨大而柔軟的雙手,並用柔和的聲音和你交談,那不够真實的氛圍,使你有面對聖者的感覺。在他居住的北京東城舊四合院平房內,那經過數十年的收藏而無法計量的文字資料堆至房頂。他本人有驚人的記憶力,任何時候,只要你需要,都可以通過他在房子內的搜尋,找到想要的歷史資料,就我所知,他的收藏極富遠見,幾乎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之後所有的地下出版物和資料。他有民主牆時期出版的各種地下刊物,他也是收藏最多文化大革命時期地下詩歌手稿的人。然而,他付諸一生心力收藏的這些資料,在他悴然而逝,在我們這些愚鈍的文學工作者未及清醒地預感到什麼的時候,已全部作為垃圾,被他的家人送到廢品收購站,隨後,也許化成了紙漿,永遠地消失了。
我不知道這個世紀的文學後人將怎樣看待這一好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不僅僅是由於我這一代地下文化中人的遲鈍和愚蠢,更是對這種愚鈍的報應,這一歷史中最重要的文化遺產及文獻也許永遠地消失了,這種毀滅和消失,甚至都不是宿命般統治我們的政權去做的,而是我們自已的自毀。僅僅從這個意義上,是否已註定了一種不詳之兆,中國的地下文化和地下文學將是一個虛無的幻影,或者,這是一個警告,如果我們不善加的保存,地下文學中最寶貴的那些作品將毀滅在我們自己的愚鈍和無知之中,那真是我們的原罪。
所以,我必須說,是我置身的這一歷史———地下文學的歷史,使我站在這個講壇上具有了某種重量,這種重量意味著,我並不僅僅是一個個人,我在用我的倖存〈這倖存的後面累壓著難以計量的不幸和苦難,排列長長而後續不斷的,幾乎是自生自滅的文學作品和一個個人〉為我們這部份人的歷史作證。
一、 地下文學中的個人
地下文學歷史中的這些作家〈我們可以使用許多特定的稱謂,如:反动文人、異議作家、地下詩人、匿名作家、戀字癖者、非主流作家、抽屜文學寫作者、從未被官方承認的作家等等〉,感謝人類誕生了綱絡(Internet),否則,他們從不見經傳,甚至在一般的鉛字記載中也鮮少出現。他們中的一些人則是文學這條不歸路上的徇道者,而他們留下的文字會被國家的警察用最快的方式收繳,或者,由於極權統治的殘酷而被作者自行銷毀,隨後以最快的速度遺忘,這種例子極多,描述悲慘顯然不是我在這個講壇上的目的,但我仍想向你們舉出一些名字和他們的遭遇,或真或假,有待我們的考証。
郭世英,中國地下文學歷史中最早的徇道者。地下文化沙龍「X社」創辦人,
黃翔和啞默(待補),黃翔,
郭路生,中國最早的地下詩人,七十年代神經失常,迄今已在精神病院度過了逾二十年的生涯。若不是找到位老伴,他恐怕將一生在精神病院度過,這是地下詩人不幸生涯的一個持久象症。他寫於一九六八年的〈相信未來〉和〈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曾在中國的一代人中傳誦一時。
上海詩人孟浪曾是國內重要的地下詩人和地下文學刊物出版者,自八十年代中以來,他因寫作和編輯出版地下文學作品,而不斷受到他所在地上海的警察的秘密偵察和監控。一九九二年四月,他與另一位上海詩人默默被上海警方秘密拘留並從他們各自家中搜查扣留將人財物〈主要是創作手稿、書信和地下文學出版物〉合計二百逾種。在被秘密關押了三十六天後,警方將他們釋放。此後,孟浪在上海及在中國國內的工作、旅行等一直受到騷擾及恐嚇,一九九四年五月起,警方加劇對他的迫害,使他不得不避走匿居。當他回到上海家中,警方即開始對他進行更繁瑣的傳訊,調查他的全部文學活動〈一度每星期三、四次,每次四小時以上,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影響〉。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五年九月他應美國布朗大學的邀請作為一個訪問作家而流亡國外。
上海的詩人京不特創作了一首抒情長詩〈第一個為什麼〉。
我想問的是,在同樣的八十年代,另一些功成名就的詩人作家們怎麼樣呢?在同樣的時間,右派小說家王蒙成為了中國政府的文化部長,據我所知,他确曾用手中的權力保護過像劉心武那樣的被官方改革派認可的作家,他曾因不慎刊發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地下小說家馬建的短篇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在最大的官方文學刊物《人民文學》上,而幾乎丟掉他在官方的職務〉。XX,一個一度有地下文學領袖聲譽的詩人,由於他那驚人的適應力,進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詩歌組,而同時,當年同為〈今天〉創辦人的芒克在北京連一間八平方米的房間都無法租到,乃至為了生計,經由朋友的介紹和擔保,以在北京復興醫院看守大門為生。在這裡,我並不只是作簡單的類比,那會把如此復雜的當代中國社會生活演繹成算術中的加減法,我僅僅是想告訴人們,在眾多的中國作家、詩人,甚至從東方到西方的政客和媒體津津樂道的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美好時期」,被某一詩人宣稱的「沒有政治壓制」的時期,地下詩人或地下文學的命運。是的,國家邪惡的象徵———警察確實不會,也不敢去搜查王蒙或XX的臥室或書房,但確實毫無禁忌的,甚至放肆而野蠻的一次次的搜查地下詩人的臥室和手稿,拘禁並監視他們,並要使他們喪失寫作和起碼的正常人的生活。這就是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地下文學和地下詩人無法逃避的命運。
真正構成中國地下文學存在基礎的主要是現代詩歌。這一小小的傳統從六十年代初始,是經這些詩人〈即使暴政的殘酷未能使他們留下作品,至少,作為名字和傳奇〉延綿下來的。在地下文學延綿不絕的小小傳統中,地下詩歌不僅僅是中國自本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新詩演進歷程中的重心,甚至,它就是一九四九年之後漢語現代詩歷史的全部,這也是國家視現代詩為異端的原因。
二、 八十年代的地下文學
如果說,一九七八年在北京民主牆上面世的貴州啓蒙社詩選及随後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本非官方文學刊物《今天》是文化大革命及整個七十年代地下文學最終結晶的話,八十年代則是地下文學在中國各個主要中心城市形成現代主義詩歌運動的最重要時期,一些偉大的文學詩篇和傑出的文學個人構成了地下文學中重要的文化遺產,經由這些作品、地下詩人叛逆性的自毀生涯,構成並確立了地下文學的美學標準,而這一美學標準首先是面對詩歌的。在這裡,我願意談到下列的詩人與作品。
黄翔,
芒克,作為中國地下詩及地下文學歷史中最早或最有資歷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天性、生活態度,乃至他的詩作,或者說由於個人性格所造成的遭遇,使他和朦朧詩的代表人物徹底拉開了距離。他不是一個如布羅茨基所說的「不時向政治領域探頭探腦的抒情詩人」。但他寫出了他一生中可能是最成熟和最具見證色彩的詩篇〈沒有時間的時間〉(1987)、組詩〈群猿〉(1986)及詩集〈陽光下的向日葵〉(1985)。這些詩當時不可能出版,也從未獲得過如他早年的〈今天〉戰友北島般在官方出版物中的幸運,這些經由地下油印出版的詩集,由地下先鋒藝術家馬德升插圖,成為當時最被珍愛的收藏。
多多,這位七十年代地下詩壇中最傑出、也最具政治敏感的地下詩人,經過多年半自閉的雙重生涯後〈在整個八十年代,白天他是一位稱職的官方報紙〈中國農民報〉的記者,並且一年十幾次的在中國廣大的鄉鎮旅行,撰寫千篇一律的新聞報導,到了夜晚和周末,他恢復了瘋狂敏感的詩人氣質,在他那套極具詩人格調的單元式公寓房內,通霄達旦的閱讀和寫作,撕碎一張張稿紙、喝酒、一根根的連續吸菸,用從未喪失的眺望原野的力量寫出了許多經典性的詩作〉。他終於走出了封閉狀態,開始尋求在地下詩壇和西方世界的雙重認可。一九八九年,他第一本地下出版的詩集《里程---多多詩選1972---1988》問世,他在
孟浪,真正承擔國家對詩人懲罰的恰恰是像他這意義上的地下詩人,這種厄運和來自國家的野蠻傷害著一個詩人日常的生活、身體、甚至心靈,但它未能徹底傷害到他的寫作,特別是他的詩歌。他寫出了對一個邪惡時代中個人命運進行追問和深刻內省的長詩〈凶年之畔〉(1986)和〈私人筆記…一個時代的消亡〉(1987)。這兩首雖在詩藝上粗礪卻極富氣勢的長詩是這一嚴酷時代真正的見證,假如政治可以廣闊的定義的話,也是描述共產主義制度下人的命運的力作。
在美學上,地下詩歌並未缺席。八十年代的地下詩歌運動除了它的浮躁、急迫和集團性外,還貢獻了它龐雜、巨大的詩歌理論,這是由一批漢語詩歌語言探險家們完成的,由楊黎、藍馬、周倫佑等人組成的四川詩歌集團貢獻了「非非主義」詩歌理論。在八十年代,四川盆地的一批地下詩人,如胡冬、萬夏、廖亦武、張棗、柏樺等人,用他們標新立異的詩歌理論,揮難霍式炫耀的才氣和詩歌語言上的全方位實驗,甚至用「魏晉風骨」或「竹林七賢」式的古代中國文人狂徒的生活方式,使四川成為八十年代地下詩歌革命性試驗和詩歌復興的另一中心。並突發出了一系列兼具強烈語言革命意識和反政治的混合的「主義」,如莽漢主義、非非主義、新古典主義、整體主義等。
總之,在詩的領域,官方的詩歌刊物完全喪失了它在美學上的影響。
而在小說方面,在八十年代地下文學中這一表面上看來的弱的,無足輕重的,甚至看來喪失聲音的領域,粗看起來確實是令人沮喪的。由於中國當代小說歷史中地下傳統的缺乏延續,它並未呈現足以和國家文學刊物相抗衡的地下小說刊物及其讀者,也未出現地下小說自身的美學。但在這方面並非全然是空白,重要的努力仍舊出現在上海,一九八五年,上海的地下作家王一梁、劉漫流、默默、京不特等人建立了「亞文化」這一區別於官方主流文學的根念,並出版了在極少數文學同行中傳閱的亞文化小說刊物及油印讀物〈木偶〉(1985出版)。
三、 九十年代的地下文學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的殘酷現實,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地下文學歷史中的一個分水嶺,群體性、運動式的,多少帶有一種浮躁和抗爭色彩的八十年代地下文學進程被向人群、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向文學射來的子彈突然打斷了,部份作家和詩人,特別是地下和前地下詩人的流亡,不管是出於對暴政再次降臨的恐懼,還是對於個人自由及在西方世界生活的強烈渴望,無疑,它使地下文學一下子分成了兩個互相呼應,卻又處境截然不同的部分。就如春秋時代孔子「道不行,乘俘浮於海」的抉擇,文學的流亡已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學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也就是說,假使流亡文學中偉大作品的產生還需要假以時日,甚至取決於流亡作家詩人的個人努力和創造力的話,文學流亡則由於兩份文學刊物〈今天〉(1990年復刊)和〈傾向〉(1993年創刊)在歐美的誕生和持續出版,形成了中國地下文學和地下詩人為出版自由努力的另一里程碑。而在中國,地下文學刊物更具流亡色彩及專業化面貌,並出現了南方詩人及南方詩歌對八十年代仍獨領榮耀的北方詩人及北方詩歌的挑戰。重要而帶有純粹南方風格的地下詩歌刊物一一誕生,如〈南方詩志〉(上海)、〈阿波里奈爾〉、〈北回歸線〉(杭州)、〈聲音〉(廣州、深圳),這些刊物與其說是一種自由出版行為,不如說是詩歌藝術上更具詩學色彩的努力。它關注的首先是詩藝、甚至僅僅是詩藝。它們的純粹、成熟,甚至在刊物設計上的質樸是和八十年代的地下刊物不同的。另一本以北京、上海為重心,幾乎聚合了全中國各地主要地下詩人為編委的全國性地下詩刊〈現代漢詩〉在唐曉渡、芒克、孟浪,默默的共同主持下在北京和上海輪流出版。這份刊物是九十年代地下詩歌用自身的詩人數量、優秀詩作的規模,頒發獨立的文學獎項和寓意深遠的刊發東歐異議知識分子哈維爾論文的方式和國家對文學的控制進行挑戰。
而帶有自身明確美學傾向的地下小說刊物〈異鄉人〉(雖然只出版了三期,仍舊是地下文學在其它領域,特別是小說中試圖突破的重要象徵。主編並創辦這份刊物的是地下小說家南方,從對語言及由語境構成的獨特氛圍及氛圍中彌漫的超越歷史時空的夢幻式頹廢及怪誕氣息上,南方都無愧於傑出的個人小說家的稱謂,不幸的是,由於警察及毫無安全感的上海城市生活不斷的對他形成的迫害和妨礙,他用告別中國移居巴黎而暫時中斷了自己的小說寫作。因此,這本獨特、珍貴又精緻的地下文學刊物從地下消失了。)
九十年代的地下文學面對著專制控制和文化商業化的雙重困難,許多詩人和作家也許仍未流亡,作品卻先行流亡了。
因為中國所處的遠離西方的地理位置,以及近代中國數百年來災難、戰爭、貧困及遭受西方列強侵害的歷史,中華民族遙遠歷史上偉大而輝煌的文化和文明並不足對抗這幾百年來的屈辱和不幸,所以,中華民族一直懷著某種對西方近代偉大文明的文化自卑感,但這種自卑感也孕育著崇拜,甚至是因為專制政治的文化封閉而強化的對另一文明想象的崇拜。嚴格的講,地下文學和地下文化在早期也是這一想象及文化崇拜的產物。這也許令人沮喪,但毫不驚奇,想想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任何的文化衝擊,甚至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降臨,都源自西方文明。重要的是它滋生的果實,讓我們看一看前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制度下地下文學的歷史,看一看這一地下文化所產生的偉大作家或文學作品,如曼德爾施塔姆(),他那影響了整個蘇俄文學和詩歌的偉大作品,竟是由他那活下來的遺孀———一個同樣偉大並罕有的堅信保存她的丈夫的作品是她活下來的全部意義的女性保留下來的。她不僅留下了他的詩和散文,還留下了她撰寫的描述偉大詩人的勇氣、生活和遭遇的回憶錄。其他人,如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和索爾仁尼琴等,他們不僅是地下文學或流亡文學中的偉大傳奇,也留下並出版了偉大的作品。再想想其他的東歐作家,捷克的哈維爾、瓦楚里克、昆德拉,波蘭的米沃什、赫伯特()等人時,中國的地下文學或流亡文學就不會感到孤立和不幸了,如果說中國的這一小小的地下文學傳統仍太單薄的話,我願意將這一地下傳統的精神紐帶和前蘇聯、東歐地下文學傳統相連接。這一地下傳統超越了國界和地域,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制度對文化摧毀狀況下文化強大生命力的某種奇蹟,這種文學生生不息的火焰,這來自地下的聲音不應被世界忽略。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刻,處於流亡狀態的文學人文雜誌〈傾向〉的誕生,構成了一種象徵和使命。西方世界,特別是作為文明的最後堡壘的大學和知識界,應該聽到這充滿創造性內含的獨特聲音,這野生和頑強的地下之聲會給人類的現狀及未來注入一種想象和活力。這可能是二十世紀末最奇特的聲音,讓我還是引述約瑟夫.布羅茨基的預言,文學———特別是國家視為異端的文學,應比國家更為攸久。
我在這裡探討的地下文學主要是以詩和詩人為標志的,是以詩所產生的時代為其解析背景的。基於我們所處時代的嚴峻性〈至少對於獻身詩寫作的詩人〉,同樣基於時代對於個人命運及文學創作想象力上所構成的嚴峻性,這裡舉出的詩作不是一般意義上個人閒情逸致的詩作,這種寫作至少在我這一代詩人中已不構成主要內含,我指的是詩歌是現代意義上的,更多的是某種充當了時代內在見證,並在詩藝,也就是詩的想象力極限上對詩的結構、語言及意象張力上均予以創造性強化的詩作,我的時代及我們當代的文學世界必須承受詩歌對它的介入。詩在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發展中的邊緣化,甚至廣義上詩人數量減少並不能影響詩的內在的、更為復雜的深化進程。而地下詩歌,或者說發表或出版在民間文學同仁創辦的刊物上的詩,正是這一類詩歌最為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是現代詩歷史的全部。
當然,詩歌從不應該只是詩人對於個人境遇感性的平面描述,詩在這一時代也不僅僅是「復雜經驗的聚合」,它還是一種警示,一種存在境遇的見證。
當人們審視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時,有一個部分是必須面對的,這一文學歷史中充滿了苦難、不屈不撓及其傳奇,這是我這一代人的文學,我稱之為——中國的地下文學。它的歷史以及其中出現的許多詩人和作家,構成了另一個文學傳統,而這一傳統由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國大陸恐怖的政治環境下許多作家的逃亡,由此產生了另一重要的文學形態,即,在中國之外的流亡作家以及流亡的文學,已更多地為世界所知。所以,我可以這樣地宣稱,中國的地下文學,它的作家、它倖存下來的作品,它充滿苦難和被遮蔽的歷史,將和官方出版物中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及御用文人所陳述的中國文學形成對比。已終將成為當代中國文學歷史中一個偉大的存在。
地下文學的起源和產生背景
嚴格地講,一九四九年後仍漸漸出現的中國地下文學主要地呈現為地下的詩歌,它包括了地下的詩歌刊物、地下的詩歌出版物及不斷出現的地下詩人聚會及朗誦會,詩人,擔當了地下文學歷史中主要的角色和見證。
最近的證明就是被中國廣西省的公安及地方政府強行禁止的一場籌備了近半年,全國各地逾二百位詩人及詩歌批評家應邀參加的「中國新世紀詩歌發展」研討會,因為其中的逾百位詩人及參加者都曾創辦過地下詩刊,在地下的詩刊上撰稿,出版過地下的詩集,這一被稱為世紀末現代詩盛典的文學活動,以三位青年詩人魏滿增、蔣楠、王長懷的短期被捕及政府的禁止而成為世紀末中國的又一次文學迫害事件。
地下文學最初的發端應該是在六○年代初,但幾乎已難以找到可供考證的文學作品,只留下了當事人——那些青年詩人及作家對悲慘遭遇的回憶。從年齡上,現已流亡美國的貴州詩人黃翔是最早也是最年長的地下詩人,他留下了作品,其中一首詩中的兩句構成了對那一個時代象徵般的見證:「即使我祇僅僅剩下一根骨頭/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六○年代初,在北京的兩個最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是以當時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為核心的「X社」(1962-1963年),以及另一個地下文學沙龍團體「太陽縱隊」(1963-1966年),它的主要組織者為當時的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張郎郎(左翼畫家張仃之子)。但是,兩個文學團體的組織者和參與者為此付出了悲慘的代價: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許多文學青年祕密地閱讀流散到民間的禁書,特別是譯成中文的西方文學和哲學、歷史書籍,形成了地下文學的第一個高潮。在四川成都地區,六○年代文革時期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野草詩社,其中的詩人有鄧懇、蔡楚、杜九森、陳墨、馮里、樂加等。他們相識於文革中成都的地下書市,他們的作品也流傳於當時的四川地區。最著名的地下詩人是二十歲的北京中學畢業生郭路生(食指),他寫於
文革中的地下文學
七○年代初,地下寫作及地下詩歌的興起以北京、上海、成都等許多地方的地下文藝沙龍和傳閱禁書作為它的精神溫床,地下詩人依群(齊雲)在一九七○年前後寫下了以紀念法國巴黎公社起義一百週年為主題的數首政治抒情長詩。而集聚在河北省白洋淀地區的一批下鄉知識青年中,三位青年詩人寫下了各自重要的作品,根子(岳重)從一九七○到一九七三年寫出了〈三月與末日〉、〈深淵上的橋〉、〈白洋淀〉等八首長詩,芒克(姜世偉)則寫出了詩集《綠色中的綠》,代表作為組詩〈天空〉和〈十月的獻詩〉、多多(栗世征)則寫下了帶有叛逆及強烈見證色彩的詩作,代表作為〈教誨——頹廢的紀念〉和〈同居〉。同時,在北京的青年詩人方含(孫康)、江河(于友澤)、嚴力、林莽、北島(趙振開)等許多人也開始了文學創作。
以石默、艾珊為筆名,北島在文革後期寫作的中篇小說《波動》,以類似電影中蒙太奇式的鏡頭切換,塑造了幾位具有小資產情調強烈時代烙印的城市青年人,他們在如此壓抑和暗淡的紅色政治恐怖下仍舊閃現的情感光亮和對政治環境的獨立思考成為小說的主題,我認為,《波動》是當時地下小說中最深刻也是最具存在主義色彩和異化情調的文學作品。另外,當時在地下流傳的情色小說《曼娜回憶錄》、《第二次握手》、金觀濤和劉青峰的思想性書信,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地下文學。
所有這些文學作品,主要是詩歌,在六○年代和七○年代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學生及下鄉落戶的青年知識份子中傳閱傳抄並廣為流傳,這是整個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唯一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呈現,它奠定了地下文學最初的傳統,形成和發展出了一種和謳歌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黨武裝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革命浪漫主義文學格格不入的以叛逆和懷疑乃至色情的審美風格和文學表現形式,並為一九七八年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標誌的地下文學刊物的出現做好了文學和作者的雙重準備。
一九七八年底,地下文學刊物《今天》文學雙月刊在北京創刊,這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出現地下出版並且發行的文學刊物。一九八○年底,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在整整兩年的時間裡,共出版了九期刊物和三期「文學資料」,每期約印刷一千冊。作為地下文學在北方中國最重要的呈現:它發表和出版了一批地下詩人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詩人芒克的詩集《心事》、北島的詩集《陌生的海洋》、江河的詩集《從這裡開始》、北島的小說集《波動》以及詩人白魔(多多)、顧城、舒婷、楊煉、嚴力、食指、白夜、小青、方含等人的詩作,萬之(陳邁平)、王力雄、甘鐵生、史鐵生(金水)、石濤等人的短篇小說。
八十年代地下詩歌高潮期
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經過了五年左右地下文學的潛沈期和文化控制的嚴酷期之後,從一九八五年前後開始,地下詩歌以全國性運動的方式前所未有地呈幅射狀展開,構成了圍繞北京地區、四川地區和上海地區的三大文學重鎮,並形成了地下詩歌的又一高潮,這一時期重要的地下詩人和地下刊物編輯有:北京地區的多多、芒克、黑大春、貝嶺、馬高明、雪迪等,重要的地下詩歌出版人和編輯老木於一九八五年編輯出版了地下詩歌的完整收集本《新詩潮詩集》上、下冊。在上海地區重要的詩人有孟浪、陳東東、陸憶敏、王寅、默默、劉漫流、韓東(南京)、呂德安(福建)等,他們創辦了數本地下詩歌刊物、如《海上》(1985-1990年,共出版四期)、《大陸》(1985-1988年,共出版十三期)、《他們》(1985-1997年,共出版九期)等。在四川地區的重要詩人有柏樺、黃翔(貴州省)、翟永明、廖亦武、楊黎、周倫佑、蘭馬、歐陽江河、萬夏、胡冬、唐亞平(貴州省)等。他們出版有《非非》(1986年)、《中國當代實驗詩歌》(1987年)《漢詩,二十世紀編年史》(1987年)等刊物及集刊。
在八○年代後期,有兩份重要的詩歌刊物在北京創刊,一批美學見解相近的青年詩人陳東東、張真、老木、西川、貝嶺等創辦的《傾向》詩刊(1988年),在它的發刊詞「傾向的傾向」上寫道:「以嚴肅的態度發現並有所發現。這就是傾向的傾向……是基於詩人的理想主義信念和知識份子精神……它更多地展現在他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上。」由北京詩人芒克、楊煉、林莽、多多、雪迪及詩評專家唐曉渡等組成的「倖存者」詩人俱樂部創辦的詩刊《倖存者》(1988年)。這些刊物一般只能出版二至三期,隨即便會被各地的公安局以出版非法刊物的名義勒令停刊。
八○年代末的一個重要地下文學事件是已停刊八年的《今天》文學雜誌在剛剛從歐洲居留歸來的原主編北島主持下,於
八十年代的地下文學主要是以詩歌為標誌,以地下詩歌刊物為表現形式。但隨著一九八九年六月全國性的學生及市民要求民主的抗議運動被政府及軍隊殘酷鎮壓,地下文學活動及地下詩歌刊物,在短時間內幾乎全部停止了。許多地下詩人及文學刊物的創辦人相繼逃離中國或因此選擇滯留國外。《新詩潮詩集》主編,也是《傾向》詩刊創辦人之一的老木逃往法國;詩人江河、貝嶺滯留美國;詩人多多在
九○年代的地下文學刊物與作家群
從一九九○年始,地下文學活動及地下文學刊物再度出現,並形成更為專業化及更具流派特色的地下出版活動。在更多的地區,而不僅僅是成都、上海、北京三大文化中心,從一九九○年至二○○○年十年中,先後已有逾一百種不同的地下文學刊物、集刊及書籍不定期出版。而且不僅限於詩歌刊物,還包括小說刊物、攝影專輯、現代音樂刊物、藝術刊物等,在文學領域,已形成和國家的文學刊物及只在官方的文學刊物和出版社上發表作品的作家抗衡的地下文學刊物及地下作家群。一些重要的地下文學刊物影響了許多的地下作家,一九九○年,上海的小說家南方創辦了一份在三年內僅出版了兩期的以小說為主的地下文學刊物《異鄉人》,《異鄉人》上的小說在風格上更為獨特,完全迥異於官方主流文學刊物上的小說,從一開始便確定了自身的小說美學,從某種意義上填補了地下文學刊物中甚少出現小說的空白。
由三十多位中國各地的詩人共同擔任名義編委的地下詩刊《現代漢詩》,在芒克、唐曉渡、孟浪、默默主持下,於一九九一年春在北京創刊,前後共出版了九期。《現代漢詩》曾頒發獨立的詩歌獎「現代漢詩獎」,此獎獲獎人為孟浪(1992年)和西川(1994年),這份刊物每期印刷二百五十冊,在全國各地的地下詩人中流傳,後來由於孟浪,默默在上海被捕,於一九九六年停刊。
一九九七年四月,由四川詩人廖亦武和蔣浩等人創辦了極富人文色彩的文學刊物《知識分子》,刊發小說、詩歌及思想性論文,佔相當篇幅的譯文全部轉載自在海外出版的《傾向》文學人文雜誌,重點發表了異議知識份子作家哈維爾的許多文章,以及納粹反猶大屠殺的悻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作家埃利.維塞爾的散文等,它的思想性已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地下文學刊物,此刊物只在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各出版一期,每期約印刷兩百本,隨後便被四川省公安局禁止出版了。
一九九九年,「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立場」兩大詩人群的論戰和對峙是地下詩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辯論,由於現代詩歌在文化領域日益邊緣化,構成了地下詩人群體性的焦慮和對知名度的強烈敏感,由一九八八年創刊的《傾向》詩刊及《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前後提出並予以闡釋的「知識分子精神」後來被異化為歐陽江河、王家新、西川、唐曉渡、張曙光、程光煒強調的「知識分子寫作」和以于堅、韓東、伊沙、沈浩波、楊克為代表的「民間寫作」群體之間在詩歌作為事件、文學的功能、詩歌的能指和所指的關係、詩在這一時代中的角色及話語權力的爭論,隨後演化為誰在通過寫詩和論說獲取名利的相互攻擊性質的、頗為情緒化的筆戰。一九九八年由詩人中島創辦的《詩參考》雜誌詳細收集了以上爭論中發表的文章及背景資料。
一九九六年創刊的綜合性地下藝術刊物《文化與道德》是由在廣州的藝術家苟紅冰、趙大勇及在上海的地下作家阿鍾創辦並出版的地下刊物,但每一期的出版周期都頗長,迄今已出版了四期、最新的一期出版於二○○○年十月。這份刊物的設計和美學趣味受到了海外《傾向》雜誌的啟發,集中刊發國內地下作家、詩人和藝術家的作品和現代藝術評論。
縱觀中國的地下文學,可以這樣講,幾乎所有有成就的詩人都是地下出身,並始終游離於官方主流文學刊物之外。中國大陸的現代詩歷史幾乎就是一部地下詩歌發展史。而在小說等文學領域,地下文學則相對較為薄弱,中國大陸的小說家幾乎都是以加入官方作協、在官方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尋求官方出版社出版小說集來呈現其水準和成就。在這裡,我要談到一個幾乎是唯一的特例,小說家康赫,他剛剛完成了一部重要的長篇小說《斯巴達,一個南方生活的樣版》,帶有《尤利西斯》(愛爾蘭小說家詹姆斯.喬依斯的代表性長篇小說)式的恢宏,甚至艱澀,在文體上充滿創新,並呈現了個人風格,它向世人展現了粗俗的資本主義商業性變化中,中國南方沉淪扭曲的現實畫面。他的小說從未獲准在官方的文學雜誌上刊發,也不被認可,可他無疑將是這一時代最重要的小說家。他是地下文學傳統中的一員,他作品的價值終會被後人認識到。
九○年代後期,由於中國社會的急劇商業化,許多地下詩人進入經商領域,同時,官方出版社面對市場化的壓力,為了賺錢竟然出售國際書號(ISBN),使地下文學開始了地上化的勢頭,許多原來無法出版或只能地下出版的詩集、回憶錄、文選,通過買書號及書商和二渠道的發行,均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出版,這些由地下詩人或作家編輯,在官方出版社買了書號自費出版發行的書籍基本上延續了以往地下文學出版物的內容但弱化了精神形式,值得研究的是,這種地下文學地上化現象有別於前蘇聯及東歐地下文學的歷史,是目前中國大陸特殊的出版審查制度下的新特點和新形式。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幾本書籍有,一九九四年八月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地下詩人、個體書商萬夏、瀟瀟主編並出資買書號分為上、下卷,厚達一千多頁的《后朦朧詩全集》。由地下詩人廖亦武編選,以買書號及書商出資印刷,系統介紹七○年代地下詩歌歷史的回憶錄《沉淪的聖殿》(1999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許多地下詩人也通過買書號,自費出版詩集。
地下文學的地下出版和地上化構成了一種全新的文學景觀,地下文學隨著出版體制的商業化,特別是由於網路文學與網上文學刊物的興起,彼此已互為滲透,地下文學的內在精神、獨立的價值尺度和美學趣味仍然將不斷地面對專制制度和商業社會的多重挑戰,它的未來正在變化之中,但它已成為二十世紀世界文學歷史中獨特的一個部份,在新的世紀中,我將密切關注它的發展。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会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