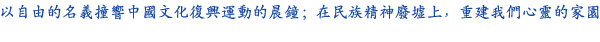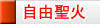附錄文章1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詩歌
貝嶺
除非這北半球的文明為未來的考據學預留了某些塵封的奇蹟,或者出現某個神話如同在共產主義俄國發生過的,一個文學天才的遺孀或後代緊握一隻收藏他(她)全部作品的中國式炒鍋,仍在佔人類五分之一的國度裡東藏西躲。假如沒有,那麼,逾時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1976)期間出現的地下文學(嚴格上講是地下詩歌),可能是那個時代唯一的文化遺產。然而,就像罪惡的無處不在使得人類無動於衷一樣,這一重要的文化遺產繼續被遺忘著,以突顯作為見證人及遺產繼承者的無能與罪咎。
由於那些地下文學創作者及收藏者的珍愛與遠見,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保存下來了一部分文學作品,並在70年代末至今的十八年中陸續通過地下印刷及可能的正式出版匯集成冊。它使作為傳說的地下文學不再僅僅成為傳說,並且證明,在時而嚴酷時而略顯寬鬆的極權中國,地下文學通過它的作品、出版物、及不幸的作者,形成了自身的文學歷史,它甚至可能被後來者視為一項偉大的文學傳統。
一:六十年代早期作為傳奇的地下文學活動
地下文學最初的發端應該是在六十年代初,但幾乎喪失了所有可供考證的作品,只留下了當事人對悲慘遭遇的回憶。目前已知最早的地下文學團體是以當時北 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郭世英(郭沬若之子)為核心的「x社」(1962-1963年) (1)︰「x社」實際上是由幾個北京青年學生為探討哲學和文學問題而聚合起來的小團體,成員還包括張鶴慈、金蝶、牟敦白等中學生或大學生。目前為止,「x 社」成員的文學作品只有由萬伯翔(萬里之子)以手抄形式留下的郭世英寫的日記作為郭沬若的遺物留存下來。
幾乎在同時,另一個地下文學藝術沙龍「太陽縱隊」也在北京出現。這種類型的沙龍其實是大學生、文學青年及青年畫家的家庭聚會,但卻極大地激發了這些 年輕人的創作。據「大陽縱隊」的主要組織者張郎郎(2)回憶,這一地下文藝沙龍持續的時間較長(1963-1966年),主要參加者中有一些在今日中國及 西方頗有些名聲的藝術家,如畫家袁運生、丁紹光、張士彥、學者巫鴻(芝加哥大學藝術系教授)、吳爾鹿(藝術品鑑定家)、以及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張文興、張新 華、董沙貝、于植信、張潤峰、周七月、張寥寥、耿軍、鄔楓、蔣定粵、張大偉等。他們在當時甚至出版了只在少數朋友間傳閱的手抄刊物。
據現有的零散資料及當事人的回憶,文化大革命前形成某種影響的地下文學活動及沙龍僅此兩樁,且都在北京。參加者許多是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及御用文 人、畫家的後代。作為追求文學自由和表達自由最早的形式。許多上述活動的組織者為此付出了悲慘的代價。在某種意義上,這個景象是那個邪惡時代最為殘酷的死亡意象------「x社」組織者郭世英於
以閱讀禁書,獨立思考,秘密聚會及地下寫作為特徵的早期地下文學活動,雖然形成於六十年代初期,但遭受徹底的禁止與懲罰則是由文化大革命中的國家執法機構及當時的紅衛兵組織予以完成的。
「X社」的張鶴慈(北京大學學生)、牟敦白(中學生)因此被捕坐牢,「太陽縱隊」的張郎郎(當時為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及地下文藝術沙龍的組織者周七月分別以「里通外國罪」及「反革命罪」被捕,判處死刑緩期,並坐了整整十年監獄。
除了當事人記憶中零散的詩句、殘簡及作品題目,以上作者所有的創作手稿均被北京市公安局在查抄時沒收。故,從目前的資料看,文革前的地下文學沒有任何完整的文學作品留存下來。
二:六十年代後期及七十年代初地下文化活動的再次興起
被毛澤東及他的激進追隨者稱為「暴風驟雨般」,並要「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文化大革命,由於它要摧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以外的一切思 想和文化。甚至連1949年之後的十七年中產生的歌頌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文學(文革中被稱為修正主義文學)也同樣受到了批判,並成為禁書,這使當時的中國大 陸幾乎成為文化的沙漠和廢墟。然而,沙漠與廢墟在某種意義上強化了人的饑渴感,為有心人提供了找尋文化遺物的可能,地下文學的第一高潮,正是這樣出現的。
文化大革命前由國家出版社內部出版,並只限於提供給共產黨高級幹部及文化官員進行批判用的內部書籍,主要是西方的哲學、思想及文學著作,如在六十年 代初由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內部發行的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美國哲學家懷特(Morton G.White) 的《分析時代》,美國小說家塞林格(J.D.Salinger)的小說《麥田上的守望者》,蘇 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人物傳記,「解凍文學」作品及持不同政見者的著作,如南斯拉夫的異議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德熱拉斯 (M.Djilas)的《陸准》,蘇聯作家愛倫堡 (I.Ehrenbrug)的文學回憶錄《人、歲月、生活》,蘇聯小說家阿克肖諾夫的小說《帶星星的火車票 》等封面為灰色,被閱讀者戲稱為「灰皮書」的一批書籍。由於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的抄家暴行,被沒收流散到社會上,使這批書從共產黨原來官 僚結構中的高層流入到了民間,在青年學生及下鄉青年的不同群體中傳閱,形成當時青年人中最早的閱讀高潮。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地下文學主要的摹仿來源及文化資源,甚至許多作品的風格,大都受到這批流落民間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哲學和一些回憶錄,及早期俄羅斯文學與後來的蘇聯、東歐國家政治異議分子的著作及文學作品的影響。
從散亂的資料及許多當事人的回憶中可以發現,地下文學曾經在幾乎是文化空白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形成了某種高潮。
首先,文化大革命以強迫的形式把青年學生用插隊落戶、大串聯、去兵團從軍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為書籍的流傳,作品的討論及寫作的彼此影響創造了條件。
其次,由於青年人從邊疆及農村集體性回家探親及逾期不歸,大城市中出現數目更多的地下文藝沙龍和家庭聚會,青年知識分子在其間頻繁地交談,展示作品及交換禁書,使得寫作,特別是詩歌創作以手抄筆記的形式流傳著。
在曾經是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上海,源於對書籍的渴望,一些文學青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6年春到1968年6月),開始了持續的地下聚會。根據 現在美國哈佛大學讀
長記那些奢靡而醉心的歲月,
沾染了歡讌時傾觥的酒珠。
浸濕了長門妃子夜怨之淚,
染成你如今殘脂駁落的哀容。
像景陽樓早妝的鐘聲沉墜而消歇了,
像那溝水上的柳影隨斜陽而消逝了,
地下的高唐客還悵望江上的雲雨嗎﹖
記取吧,如銅駝夜哭於荒野的荊棘。
雖起始於幼稚的模倣,但多種形式的嘗試不僅伴隨美感經驗的欣喜,亦創造與不朽的意欲相連。實察上還不知道應該寫什麼,寫出的東西卻不自覺地重複出現死亡的主題或意象。」
這些詩作迄今仍湮沒無聞。後來陳建華收入他出國後用電腦打印自編的詩選《紅墳草》中。
文化大革命早期最著名的北京地下詩人是作為中學生的郭路生(食指),他寫於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動。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
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築
突然一陣劇烈地抖動
我雙眼吃驚地望著窗外
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的心驟然一陣疼痛,一定是
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
這時,我的心變成了一隻風箏
風箏的線繩就在母親的手中。
線繩繃得太緊了,就要扯斷了,
我不得不把頭探出車廂的窗欞。
直到這時,直到這時候,
我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陣陣告別的聲浪,
就要卷走車站。
北京在我的腳下,
已經緩緩地移動。
我再次向北京揮動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領。
然後對她大聲地叫喊,
永遠記著我,媽媽啊北京﹗
終於抓住了什麼東西,
管他是誰的手,不能鬆。
因為這是我的北京,
這是我的最後的北京。
從文本上看,這是一首押韻,適宜朗誦,並有著強烈內在旋律的白話詩,全詩從頭至終,均為四句一段,每一段都采用白描手法烘托那四點零八分出發的列車 離開北京前,一個即將遠離北京的知識青年(詩人本人嗎﹖)對於母親和北京互為交錯的深切悲傷之情。整首詩的所指清晰,象徵明確,尚未受到現代主義詩歌的明顯 影響。此詩當你吟誦時旋律感極強,而且押韻,幾乎不需要任何背景暗示,那如紀實鏡頭般的畫面便出現了。
如果說郭世英是地下文學歷史中第一個為此獻出生命的詩人。那麼,郭路生則是地下文學歷史中最早留下作品,並被廣為傳頌的詩人。由於文化大革命既毀滅 文化,又消滅肉體的殘酷性,郭世英的詩作我們只看到一首,而且還是兒歌。而郭路生由於未組織社團,因而留下了詩作和生命。據說他是當時唯一同時參加六十年 代初地下文藝沙龍和文化大革命中地下文藝沙龍的詩人。
真正為郭路生帶來經久不衰的聲譽,並被後來的地下文學圈視為現代詩先驅的是他的《相信未來》一詩。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當我的葡萄化為深秋的露水,
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
我依然固執地用凝露的枯藤,
在凄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
我要用手指那湧向天邊的排浪,
我要用手撐那托住太陽的大海,
搖曳著曙光那枝溫暖漂亮的筆桿,
用孩子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
我之所以堅定地相信未來,
是我相信未來人們的眼睛,
她有撥開歷史風塵的睫毛,
她有看透歲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們對於我們腐爛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悵,失敗的痛苦,
是寄予感動的熱淚,深切的同情,
還是給以輕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諷。
我堅信人們對於我們的脊背,
那無數次的探索、迷途、失敗和成功,
一定會給予熱情、客觀、公正的評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著他們的評定。
朋友,堅定地相信未來吧,
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
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
相信未來,相信生命。
一九六八年
郭路生早期所有的詩作全部為四行一段,結構規範,詩的語言凝鍊,但在抒情純度和悲哀的廣度上幾乎可以一下子攫住任何一個讀者,並使你必須和詩人一起 付出昂貴的情感。如同詩人多多所說︰「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詩的純淨程度上來看,至今尚無他人能與之相比。」儘管他早期的詩仍舊是浪漫主義文學形式下的抒情詩 類型,而且受俄國普希金詩歌漢譯風格的影響,但詩中的意象已出現疊加如︰「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餘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灰燼的餘 煙」作為描述,當它通過跳躣轉換成「貧困的悲哀」時,整句詩已不再是直陳的形容,而上升為意象。同樣,「我要用手指那湧向天邊的排浪」,「搖曳著曙光那枝溫暖漂亮的筆杆」,排浪涌向天邊,曙光被意象化為「漂亮而溫暖的筆杆」,這些象徵通過排比的意象群依次遞現。儘管郭路生當時主要的詩作證明他仍是一個浪漫 主義抒情詩人,但從他寫作《相信未來》的時間來看,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而在中國大陸中斷的新詩向現代詩過渡的形式革 命,他雖不自覺,卻是最早開始的。
儘管《相信未來》這首詩反復表達了一種對未來的抽象相信,但整首詩中彌漫的悲哀,對現實的失望和強烈的主題暗示,及他 隨後的詩作如《瘋狗》、《魚群三部曲》等已不僅僅是對文化大革命、對人的命運造成毀壞的懷疑,也 暗示了自法國象徵主義詩人波特萊爾詩作為始的現代主義詩歌的主要精神和哲學基礎---即對一切現存制度和人類關係的本質性懷疑。據說,他的詩曾在1970 年初遭到文化大革命女旗手江青的點名批判。
郭路生的詩歌,在北京、上海幾乎同時出現的地下文藝沙龍和聚會,以及由此激發的下鄉落戶青年和城市社會青年的秘密閱讀禁書熱潮,為七十年代初的地下寫作高潮,特別是「白洋淀詩派」的形成打下了伏筆。
在整整十多年中,《相信未來》這首詩在中國各地的青年中秘密傳抄,流傳甚廣,無數的知識青年在精神苦悶,前途暗淡的漫 長歲月中,有時靠吟誦或抄寫這首詩來寄望未來,尋求生活下去的希望。我以為《相信未來》等詩的產生和流傳,在某種意義上成為 地下詩歌的始源。而郭路生本人的不幸遭遇,他瘋狂的戀愛故事,乃至他從七十年代初開始逐漸精神崩潰,間斷性地成為精神病人,最後自願選擇精神病療養院作為 歸宿的結局,成為文化大革命時代地下詩人中最具傳奇色彩的生命體驗。
終於,地下沙龍在七十年代初再次出現。1970年是法國大革命歷史中的巴黎公社誕生一百週年,為了強調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巴黎公社宣稱打碎 一切國家機器,徹底消滅一切等級制度的精神繼承性,中國共產黨在當時曾使用全部宣傳機器來介紹和紀念巴黎公社。繼郭路生之後,政治抒情詩人依群(齊雲)寫 下了《紀念巴黎公社一百週年》等數首詩作,一時成為當時地下詩壇最為矚目的詩人。
巴黎公社節選︰
奴隸的槍聲嵌進仇恨的
一個世紀落在棺蓋上
像紛紛落下的泥土
巴黎,我的聖巴黎
你像血滴,像花瓣
貼在地球蓋色的額頭
美麗的夕照浸著奴隸的血滴
驕傲的逝去了
黃昏包圍著拉雪茲
這是最後的巴黎
終於在仁慈的硝煙中
升起了梯也爾無恥的旗
啊﹗拉雪茲----不朽的巴黎
可惜,槍聲從這裡沉寂
中斷了----
這僅僅是序曲
這偉大的前奏之後
悲壯的交響樂
將穿越一個世紀
啊﹗拉雪茲---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風、是閃電
雖然終於消失在黑暗裡
但是這就夠了﹗夠了﹗夠了﹗
你劃時代的一閃
開辟了整個一個世紀
啊﹗拉雪茲----高貴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個世紀過去了
滿腔熱血化成了五月的鮮花
開在黃的、黑的、白的國度裡
傍晚又降臨了
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納河灑滿素色的花環
若以明確的現代意象入詩來描寫政治歷史題材的,在地下詩壇----依群為第一人,而且他一起手就直接切入宏大的歷史主題。所以把依群稱為地下詩壇的 政治抒情詩人。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政治抒情詩,猶其是為共產主義事業或新中國革命英雄歌功頌德的政治抒情詩十分泛濫。但依群仍以 《紀念巴黎公社一百週年》一詩震撼地下詩壇。確實,這首詩的視野開闊,意象輝煌,多多認為︰「依群最初的作品已與郭路生有其 形式上的根本不同,帶有濃厚的象徵主義味道。而依群詩中更重意象,所受影響主要來自歐洲,語言更為凝鍊。可以說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5)依群這首 詩從題材上仍舊充滿「革命性」。氣勢雖大卻不夠持貫,意境也略顯空泛。但僅就此詩意象之明確,結構意識之強,以及氣勢之磅礡來看,實為罕有之作。(直到文 化大革命後,江河創作的幾首長詩如《祖國啊,祖國》、《沒有寫完的詩》、《紀念 碑》等在藝術形式,氣魄及表現手法上更為磅礡,更富現代性,達到了此一類型政治抒情詩的極致。)依群的這首詩及其它以巴黎公社為主題的詩, 顯然深受歐洲象徵主義詩歌的影響,而且詩歌語言乾淨凝鍊,似可視為有意識地進行詩歌形式革命的現代性作品。
地下詩歌以七十年代的依群詩作始,開始進入它的全盛時期,並以北京的地下文藝沙龍為它的精神溫床。特別是1972年,出現了以北京的一位名女人,當 年老紅衛兵的代表徐浩淵主持的音樂(訓練和比試美聲唱法),現代畫與書籍交流研討及比試各自詩歌的沙龍,以及同時期完全開放,任何人都可登門造訪,更集中 在對個人命運及國家前途的探討及交換禁書,系統收集地下文化資料的趙一凡家的沙龍,並由此催生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稱為「白洋淀詩派」的地下詩歌。
而在同一時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紅色恐怖達到了新的高潮。1970年初,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文革和中共中央在全國掀起了批判劉少奇為代表的「地 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的高潮。同年2月,在全國展開「一打三反」運動,到同年11月,共揪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萬人,逮捕了二十八萬五千 多人,許多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刑。」(6)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地下沙龍開始出現,1972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飛機失事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消退,政治和文化的環境稍見緩和,導致地下文學沙龍數量增加,並在1973年進入鼎盛時期。1972年開始,部分國家出版社恢復出版,並以「內部發行」方 式大量出版了一批俗稱「黃皮書」的蘇聯及西方文學,政治與歷史書籍。例如翻譯的蘇聯小說《你到底要什麼﹖》、《多雪的冬天》,葉夫圖申科的詩集《娘子谷及其它》,貝克特的劇作《椅子,薩特的《厭惡及其它》,這些書籍在地下沙龍掀起震撼。地下詩歌從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及政治抒情向現代主義傾斜,並 在河北省白洋淀的北京知識青年聚集處催生了詩歌寫作狂潮,並產生了白洋淀詩派這一文化大革命期間最重要的地下文化現象。
三:地下文學的歷史性高潮------白洋淀詩歌群落
白洋淀位於離北京三百里的河北省安新縣。由於一片片的洼地相互連接,並長年積水,故被稱為「淀」。白洋淀本身由大小不等的300多個「淀」組成,最 大的「淀」被稱為「白洋」、「燒車」、「藻乍」等。白洋淀詩派早期詩人宋海泉曾在回憶錄《白洋淀瑣憶》中寫道︰「白洋淀詩歌 群落的產生,同它本身的文化傳統是沒有必然的血緣關係的,詩歌作者群的產生在這裡,也許正是由於它的這種非文化的環境,由於它對文化的疏遠和漠不關心,因 而造成一個相對寬鬆,相對封閉的小生態龕。借助於這個生態龕,詩群得以產生和發展。(7)
這個生態龕具有這樣一些特點︰
首先,它聚集了北京中學生中一批思想敏銳的份子。他們經常在一起交流、切磋、撞擊,時時產生一些閃光的東西。以寫詩為例,他們時常就學習體會、書 籍、詩稿進行交流,就詩歌理論、詩歌形式、寫作技巧進行切磋。他們關心的領域非常廣泛︰哲學、經濟、歷史、政治、音樂、繪畫等。不同的領域之間經常互相啟 迪和借鑒開闊了他們的眼界,提高了他們的思想境界。
其次,每個村的知青基本是以原學校為單位的組合,他們各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從中汲取必要的知識信息。白洋淀這個生態龕遠不是一個封閉系統,而實實在在是一個開放系統。
第三,安新縣距北京300里,相對山西、陝西、內蒙古、黑龍江、雲南等地而言,簡直就在家門口。所以他們經常來往於北京安新兩地。外地的同學也能很 方便地到白洋淀來,進一步擴大了這種交流。僅就我村而言,接待過山西、陝西、雲南、內蒙、北京等地的同學朋友,少說也有幾十人。他們留住時間少則幾日,多 則
白洋淀詩群的根在北京。
白洋淀詩歌群落這樣一個文化現象,其本質是一種都市文化。遠而言之,它繼承了五四以來吸收西方文化創建新詩學的努力。所不同的是它減少了以往所不可 避免的工具主義的傾向,多了一些對人的存在價值和存在狀態的終極關懷。近而言之,它是對10年浩劫曲折而堅韌的抗爭。借助於白洋淀這一特殊的生態環境,結 出自己的果實。」
曾在1969年到1976年間在白洋淀插隊並開始寫詩的有岳重(根子)、姜世偉(芒克)、栗世徵(多多)、宋海泉、張建中(林莽)、孫康(方含)等 北京來的中學生。他們形成白洋淀詩人群體的核心。而另一些留在北京的青年詩人,幾乎都來過白洋淀短住或長住。並在北京和白洋淀兩地相互交流詩作。他們都在 70年代初嘗試寫詩,留在北京的詩人有於友澤(江河)、史保嘉、趙振開(北島)、馬嘉、魯雙芹(女)、魯燕生、彭剛、楊樺、嚴力等。若再加上也在白洋淀插 隊或和白洋淀詩群來往密切的畫抽象畫、研讀哲學、音樂、政治歷史及寫小說的其他北京中學畢業生,一個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最大的地下文化圈在70年代初的中 國大陸產生了。
在狹義的白洋淀詩群中,寫下最多詩作,在中國地下詩的歷史中影響大,寫作時間久,同時也在詩藝上深具水準,並能幸運地留下許多優秀詩篇的,只有芒克和多多兩人。
詩人芒克從1972年開始寫詩,至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整理成卌的並在1979年地下出版的詩集《心事》中,共收錄有 長詩、組詩及短詩十六首。據說他在此期間遺失、散落的詩篇更多。包括在白洋淀知青中流傳的一本詩集《綠色中的綠》。芒克在文 革期間的創作高潮期應是1973年,在《心事》這本地下出版的詩集中,看到並注明寫於1973年的短詩及組詩明顯多於之前或 之後年頭的其他詩作。
在這一年,他寫下了組詩《天空》,其中的第一段和最後一段分別重複了這一意象︰
太陽升起來,
天空血淋淋的
猶如一塊盾牌。
太陽升起來
天空----這血淋淋的盾牌。
我無法形容自己在70年代末的北京民主牆時期看到此詩時的感覺,我曾下意識地反復吟誦這幾句詩,腦子好像被轟炸了一般,受到強烈震撼,似乎被嵌入一 幅色彩強烈的印象派畫裡。很久很久,這幾句詩,或者說這個意象在我的腦子裡揮之不去,我被這輝煌的意象所撼。如同唐曉渡所說︰「這是新詩有史以來最攝人魂 魄,最具打擊力的意象之一」(8)假使我們再往深處想一下,在太陽作為毛澤東的專利,在一個充滿了「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這「偉大」比喻的 文革國度,芒克竟然把升起來的太陽演繹為「天空----這血淋淋的盾牌」,芒克難道瘋了嗎﹖他不要命了嗎﹖在他對於太陽完全非意識形態化的意象裡,紅色狂 熱,毛崇拜,文化大革命語匯,甚至產生它的語境都在他的詩中被消解了。而且乾淨、徹底,毫無痕跡。僅僅這首詩,芒克便可確立詩歌天才和形式革命最徹底的頓 悟者的形象。他的大部分詩作甚至帶有畫家對色塊的罕有直覺,賦予意象一種色彩,同時,他的抒情也毫不纏綿。再看他同一時期詩中大自然的意象︰
果子熟了,
這紅色的血 ﹗
我的果園染紅了,
同一塊天空的夜晚。
選自組詩《秋天》
血,作為暴力的象徵,在芒克的眼中變成了僅僅作為背景的一種寧靜的美。
芒克在文革時期寫下的另一重要詩作應是那首組詩《十月的獻詩》,全詩中無一處城市的意象,是田野、鄉村和荒涼的生活帶給一個天才詩人的完整的想像。這是那個時代最為感性的想像,一個赫子的想像。
相對於芒克詩歌中那些樸素而極富震撼力的自然意象,在同一時期,作為和芒克決鬥般每年定期交換詩集的詩人多多,卻用更為徹底、野蠻和極具政治特徵和 張力的歐化意象寫下了許多現代派詩,在已經匯集成卌,並在1988年作為首屆《今天》詩歌獎而地下出版的《里 程---多多詩選》中,共收錄了多多文革期間創作的25首短詩,2首組詩及2首長詩。
在詩藝上,多多從1972年開始寫詩時,就帶有明確和毫不掩飾的現代派詩歌風格,並大量地甚至過量地使用意象,來擴張詩的張力。他的意象強烈且猙 獰,充滿飽讀翻譯成中文的西方書籍後產生的妄想和異域意象,並在詩歌中滲透了一個思想者反叛與破壞的美,幾乎在每一首詩中,多多都使用看似毫無關聯實則張 力極大的意象。如︰
歌者,省略了革命的血腥
八月像一張殘忍的弓
引自《當人民從乾酪上站起》
馬燈在風中搖曳
是睡熟的夜和醒著的眼睛
聽得見牙齒鬆動的君王那有力的酣聲
引自《無題》(1973年)
文革時期多多的詩歌語言確實帶有一種由於密集閱讀漢譯西方書籍之後的歐化語式和句法結構。他的詩是那一時期詩人中最為複雜,最帶有政治異質性,有 時,甚至強烈釋放著那個禁欲時代罕有的色情性。那種青春的騷動與反叛,通過詩中的妄想得到某種生命力被釋放的美,愛欲(來自性的強度)和政治性在某種意義 上始終貫穿著多多的詩。應該說,多多的詩,成為文革那個「乾淨」,單調和乏味的時代最異端、最反動、最頹廢的文字。根據後來的一種說法,在文革後期一波接 一波的政治掃蕩和清洗中,多多最怕他的詩作在外流傳,一有政治風聲,他便像驚弓之鳥一樣奔到任何抄有他詩作的朋友家中,親自銷毀這些詩作,萬一有他的詩作 被公安局收繳,他也矢口否認這些詩和他有關。這種緊張的生存遊戲,有時被後人認為是膽小或神經質,但看看這些詩之「反動」和異端,這種「膽小」和緊張就毫 不奇怪了。凡經歷過文革那個殘酷時代的文化人都可以想像,那些詩是要提著腦袋去寫的,請看下面這首詩︰
無題
一個階級的血流盡了
一個階級的箭手仍在發射
那空漠的沒有靈感的天空
那陰魂縈繞的古舊的中國的夢
當那枚灰色的變質的月亮
從荒漠的歷史邊際昇起
又傳來紅色恐怖急促的敲擊聲……
1974(選自《里程》)
把這首詩的寫作置於那個年代,不需要再做文本分析,那撲面而來的,幾乎是直白的意象便已告訴了我們,什麼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跳躣感極強的意象 空間中,詩句之間已為讀者預置了任何可能的想像空間。而詩人在鋪陳那個時代特有詞匯的語境中,極其冷靜,並且把政治判斷的定語砸入了讀者的視野中。這一 切,就是文革所產生的文學語境。
四:證詞,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教誨----頹廢的紀念」
作為現代詩的地下詩歌,嚴格講,是從那些詩開始,充當了那個時代真正的見證。詩中的政治意象通過對政治極度的厭惡而呈現,乃至由於極度的厭惡而使詩人對政治加倍的關心。
多多寫於文革被宣布結束的1976年的兩首詩《教誨》、《同居》是我們迄今讀到的那個時 代最為哀婉的詩篇,它的主題,它所呈現並反複呈現的是人在那一歷史中的宿命,詩幾乎成為那個時代寓言般的悼詞,以至於當人們費力地試圖去挖掘那個時代的精 神遺產,或者尋求精神貧困的原因時,《教誨》和《同居》是最為及時,又最富象徵的注釋,是對思 想和青春在那個時代如此蒼白和不幸的強烈哀悼。而詩中昇華出來的,幾乎是一種偉大的虛無。是一個清醒的守夜者恒久的見證。
教誨
-----頹廢的紀念
只在一夜之間,傷口就掙開了
書架上的書籍也全部背叛了他們
只有當代最偉大的歌者
用弄啞的嗓音,俯在耳邊,低聲唱︰
爵士的夜 世紀的夜
他們已被高級的社會叢林所排除
並受限於這樣的主題︰
僅僅是為了襯托世界的悲慘
而出現的,悲慘
就成了他們一生的義務
誰說他們早期生活的主題
是明朗的,至今他們仍認為
那是一句有害的名言
在毫無藝術情節的夜晚
那燈光來源於錯覺
他們所看到的永遠是
一條單調的出現在冬天的墜雪的繩
他們只好不倦地遊戲下去
和逃走的東西搏鬥,並和
無從記憶的東西生活在一起
即使恢復了最初的憧憬
空虛,已成為他們一生的污點
他們的不幸,來自理想的不幸
但他們的痛苦卻是自取的
自覺,讓他們的思想變得尖銳
並由於自覺而失血
但他們不能與傳統和解
雖然在他們誕生之前
世界早已不潔地存在很久了
他們卻仍要找到
第一個發現「真理」的罪犯
以及拆毀世界
所需要等待的時間
面對懸在頸上的枷鎖
他們唯一的瘋狂行為
就是拉緊它們
但他們不是同志
他們分散的破壞力量
還遠遠沒有奪走社會的注意力
而僅僅因為︰他們濫用了寓言
但最終,他們將在思想的課室中祈禱
並在看清自己筆蹟的時候昏迷
他們沒有在主安排的時間內生活
他們是誤生的人,在誤解人生的地點停留
他們所經歷的-----僅僅是出生的悲劇
一九七六年
作為二十世紀歷史中如此罕有地要徹底毀滅所有文化及文化頭腦的一個時代,文化大革命所留下來的稀少的文學遺產中,多多的這首詩《教誨 》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是對思想及思想者在這一時代所必遭的命運,對作為懷疑論者或者懷疑本身所遭受的懲罰的寓言般地揭示。假如詩歌 必定要在某一時刻介入它所身處的時代,並無可避免地要為這一時代撰寫證詞時,多多的詩,確切地說,是多多的這一首詩,恰好和這首詩寫作的年代(文化大革命 被宣告結束的一年)一起,為這場摧毀文化的革命中願意用腦袋思想的個人的命運,留下了被他用副標題稱之為----「頹廢的紀念」。
注釋︰
(1) 請參照筱白撰《社寫郭世英之死》,刊於《民主中國》1995年5月號,總第27期。
(2) 張郎郎《「太陽縱隊」傳說》,刊於《今天》雜誌1990年第二期。
(3) 楊建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第91頁,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
(4) 刊於《今天》1993年第3期第260-261頁。
(5) 多多《1970-1978的北京地下詩》、《今天》1991年第1期第80頁。
(6) 引自楊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第83頁,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1月版。
(7) 引自《詩探索》1994年總第16期,第130-13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8) 引自唐曉渡《一個人和他的詩》、《傾向》文學人文雜誌1996年總第6期,第223頁。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会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