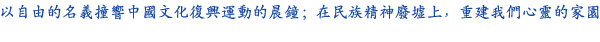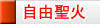八
2001年4月,我因事去紐約,我在街頭撥公用電話給蘇珊,是她助理接的電話,我問,蘇珊在嗎?她說蘇珊正在工作,請我留言。
我正要留言時,蘇珊的聲音出現了,她說近來有太多電話找她,因此她已不敢接電話,但她很高興我打來電話。那天,她的聲音難掩興奮,她說:她剛剛獲知自己獲得了兩年一度的耶路撒冷獎。顯然,她在和我分享這喜悅。耶路撒冷獎的全稱為 「社會中的個人自由耶路撒冷獎」(The Jerusalem Prize for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 我一下子未能聽懂此獎就是我以前認知的耶路撒冷獎,故反應遲鈍。蘇珊以為我不知耶路撒冷獎,便向我解釋:「這是兩年一度由耶路撒冷國際書展頒發的國際文學獎,授予其作品深刻地探討了社會中的個人自由的作家。」她感慨著:「唉,世人只知道有一百萬美元獎金的諾貝爾文學獎,耶路撒冷獎沒有說得出口的獎金,故世人不知道它在作家心目中的位置,它是文學獎中的文學獎,它頒給作家中的作家。我以獲得耶路撒冷獎為傲。」接著,蘇珊向我細數著此獎從1970年代創設以來,已獲頒此獎的有世界性影響的重要作家如:阿根廷作家波赫士62、愛爾蘭裔劇作家貝克特、法國作家波娃63、英國作家格林64、米蘭‧昆德拉、波蘭詩人赫伯特65等。聽得出,耶路撒冷獎在她心目中是崇高的。等她解釋完,向她表示深切的祝賀。我告訴她,我知道耶路撒冷獎,十多年前,在中國,我曾讀到過米蘭‧昆德拉獲耶路撒冷獎時的獲獎演說〈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66,那是一篇精采的演說,對我有著重要的啟示。她接著告訴我:「這一個多星期來,我一直在構思、撰寫這篇即將去耶路撒冷領獎時發表的獲獎演說。」
2001年的耶路撒冷獎,是對她的作家生涯、對她的文字良心,對她一生所做所為的重大肯定。
當時,我懷著憂慮看待她即將前往以色列的獲獎之行,那些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由於歷史上糾纏甚久的民族宿怨,處於極其血腥的暴力對峙狀態。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對以色列人民進行血腥的自殺式攻擊,而以色列軍隊也對巴勒斯坦居民區進行同樣血腥的暴力報復。在這一時刻,她前往以色列領獎,必定會引起廣泛的注目和非議。有友人、也有人權組織建議她拒絕接受耶路撒冷獎。
那是真正的傳世之作。鞭辟入裡、字字珠璣。是一位偉大的良心作家對文學和政治、文學和自由、文學和人等複雜關係所做的極具穿透力的論述,每一位有作家抱負的人都應該一讀再讀。蘇珊在〈文字的良心〉67這篇獲獎演說中字勘句酌地提醒文學同行:「……作家要做的,應是幫助世人擺脫束縛,警醒世人。打開同情和新的興趣管道。……提醒人們,我們可以改變。」
她無視爭議,前往以色列領獎,在獲獎演說中,她回應著要求她拒絕接受此獎的聲音,甚至回應著對她不懷好意的人:「授予某個榮譽,意味著確認某個被視為獲普遍認同的標準。接受一個榮譽,意味著某人相信了片刻這應得的。(一個人最應說的合乎禮儀的話,是自己還不算配不上。)拒絕人家給予的榮譽,則似乎是粗魯、存心掃興和虛偽的。」
她捍衛文學的多元性:「文學是一個由各種標準、各種抱負、各種忠誠構成的系統…一個多元系統。文學的道德功能之一,是使人接受多樣性價值觀的教化。」
她警示世人,「自由」和「權利」的概念正被濫用:「近年來,『自由』和『權利』的概念已遭到怵目驚心的降級。在很多社會中,集團權利獲得了比個人權利更大的重量。」
她告誡作家同行:「作家的職責是描繪各種現實、各種惡臭的現實、各種狂喜的現實。文學提供的智慧之本質(文學成就之多元性)乃是幫助我們明白無論眼前發生什麼事情,永遠有一些別的事情在此刻發生。」
她回顧著她的一生:「有三樣不同的東西:講,也即我此刻正在做的事;寫,也即使我獲得這個無與倫比的獎的活動,不管我是否有資格;以及做人,也即做一個相信要積極地與其他人憂患與共的人。」
她甚至用昆德拉式的自嘲表達著非昆德拉式的驕傲:「我所說的『完美』指的又是什麼?我不想嘗試解釋,只想說,完美令我笑出聲來。我必須立即補充,不是諷刺地,而是滿懷喜悅地。」
面對血腥的以巴衝突,她在頒獎儀式中不顧噓聲四起、退場抗議,直言力陳:「……集體責任這一信條,用做集體懲罰的邏輯依據,絕不是正當理由,無論是軍事上或道德上。我指的是對平民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器……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並儘快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裡保護移民點的軍隊,否則這裡不會有和平。」
我認為,這是她此生中最具洞見的一篇演說。
面對過去,蘇珊絕不掩飾,她勇於認錯、認真反省。在接受華裔電影導演、劇作家及文評家陳耀成的訪談中,蘇珊曾非常坦率地承認,她早年以為那些反美的第三世界國家中,那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共產黨國家中,可能會發展出一種有人性、人道的政體。在她一生中,她持有這種荒誕願望的時間大概有五年,那是她政治判斷犯錯誤的時期。她說,那些去社會主義國家訪問的人們是如此容易上當,這五年,在她的一生中似乎並不算犯錯太久。
「土星氣質的一個典型特徵表現為對自己的意志異常苛刻。」這是蘇珊在〈在土星的星象下〉一文中寫下的。蘇珊是性情中人,一方面熱情洋溢,同時,又有著對熱情的自我克制。她對自已作品的品質要求極高,故有著強烈的時間意識,有著回到工作中去的自我要求。有時,我們通話,即使話題重要,我們正談得熱烈,但一逾半個小時,她的時間警鈴會很快鳴響,她甚至會讓交談中止。如同她分析的班雅明:「若是能使工作成為自我強制的行為和一種麻醉品,憂鬱則可轉化為英雄意志。」68她常講的另一口頭禪是:「我必須回去工作了(I have to get back to work)」。甚至我們在她的家裡見面,只要時間超過一個小時,她潛意識中的那個時間閥門會合閘,她隨時會對我們說:「對不起,我必須回去工作了。」
九
每一次我去紐約,當長途汽車停在曼哈頓中國城的福州移民街區,看到滿街的福州店、福州食品、福州口音、福州氣味,那些經歷千辛萬苦來到這裡的福州新移民,正有滋有味的展開新生活。
我怎麼就成不了他們呢?我自問。
在經歷了最初重獲自由的欣喜之後,再次面對我已厭倦之極的美式生活型態,我自問:「以往的美式生活我必須再過嗎?我又將回到之前的那種生活中去嗎?」
由於一次莽撞的自由出版行為,使我在北京已重新開始的生活全部喪失。我可能買下的北京長城八達嶺鎮鄉間公寓,我想在北方鄉下過的半隱居生活,如今一切成空,一切都不可能了。可怕的是,在可見的歲月裡,我可能再也無法回到祖國。
「流放者歸來」嗎?流放者已難以歸來,流放者又被送回了美國「天堂」。
我適應不良,甚至沮喪。
我曾將這種痛告訴她,蘇珊傾聽,她理解流亡對作家意味著什麼,她認同我關於流亡也是一種命運,流亡知識分子不應僅僅關心祖國,還應該關心並介入居住國的政治、文化和生活的想法。蘇珊和我談起了我們共同推崇的布羅茨基,她為布羅茨基寫的悼文中有一句話深得我心:「家是俄語。不再是俄羅斯。」 69
家是中文。不再是中國了嗎?
蘇珊給我的建議是:「面對回不去祖國的現實,應像布羅茨基那樣,將其視之為命運。要下功夫精通英語。」她更責備我這些年來不積極尋求將自己作品的譯文在歐美的出版發表,她認為,這是流亡作家在異域保持影響力的最終方式。她不斷地提醒我:「你最近寫詩了嗎?有作品譯成英文了嗎?我可以推薦給編輯。」
她雖嚴苟,卻認可我作品的品質。她為我寫推薦信,將我的詩直接寄給報刊發表,她讓她的好友,《洛杉磯時報書評》(LA Times Book Review)主編瓦瑟曼(Steve Wasserman)打電話給我,向我邀稿,也使得我們成為好友。她將我的詩推薦給《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的文學編輯,讓我儘快將詩寄去。她介紹我認識《紐約書評》的編輯,讓我給他們打電話,問我打去了沒有,她總是說:「別不好意思,直接打電話過去,請他們給你十分鐘,告訴他們,是蘇珊‧桑塔格讓你打這通電話的。」
這些年,她一直擔憂著我的生活,問我靠什麼活下來:「我能幫助你什麼?我可以幫助你啊。」2000年秋,她為我向美國筆會中心申請兩千美元的救難生活補助,然後,不容我推辭,帶著我去美國筆會領錢。
一天,她突然打來電話,告訴我,她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書店。她說她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後,順便來到這家著名的書店,書店老闆是她的朋友,她向書店推薦了《傾向》雜誌,希望這家書店內可以有中文的《傾向》雜誌被展示和出售。她告訴我:「美國是一個有移民文化傳統的國家,書店裡應該有不同語種的書和雜誌出售。」她說:「你趕緊打電話給他,你要問他可以寄售多少書。」她掛上電話後,我馬上接到書店老闆打來的電話,他說他很榮幸得到蘇珊‧桑塔格的推薦。就這樣,《傾向》在這家書店出現了。
哈佛大學東亞系的杜維明教授一直非常仰慕蘇珊,認為她是一個在當代世界產生了真正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他請我代為邀請蘇珊到哈佛燕京學社演講,和中國學者座談,他期望能和蘇珊有一個關於東西方文明的深入對話,以探討變革中的中國和現代西方的關係。杜先生托我把這個願望轉告蘇珊,我致電蘇珊轉述了杜先生的邀請,蘇珊說,我非常願意前往,但不應是我主講,因為我對中國的瞭解不如你和杜先生,不如那些哈佛燕京學社的中國學者。請轉告杜教授,這一研討會的所有主題應圍繞著中國,圍繞著你去年在中國的經歷,圍繞著傾向雜誌的辦刊宗旨和杜先生提出的「文化中國」觀念,演講人應是你們,我去傾聽和參與討論,跟你們一起探討。」她接著問:「我的名字和我的參加可以對傾向雜誌提供具體幫助嗎?」我說:「哈佛燕京基金會有過撥款補助文化思想刊物的先例。」她讓我轉告杜先生,希望哈佛燕京基金會也能夠支持和贊助《傾向》雜誌的繼續出版。為此,她專門寫了推薦信。她說:「請轉告杜維明教授,只要我的出席和演講要能對對《傾向》的繼續出版有直接的資金幫助,何時要我去,我都去,我的演講費用可以不要。」後來,杜先生把這一資助企劃案提交哈佛燕京基金董事會,但最後還是沒有通過。也因為此,這一邀請就拖下來了。2004年,杜先生又向我提及此事,他想親自到紐約去拜訪蘇珊,與她做一次對談,可是,蘇珊已因血癌住進西雅圖醫院,此事,已成為永遠的遺憾!
2002年2月,我寫信向她通報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誕生,並以筆會創會人的身份邀請她成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榮譽會員。在信中,我談到了創辦筆會的艱難,抱怨著大量的事務性工作使我根本沒有時間寫作。她很快回信,予以熱烈祝賀,指出筆會誕生的意義。她在信中反問:「……我知道這意味著將會犧牲你的寫作時間,但你別無選擇,對嗎?筆會的成立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了,這將被看作是中國文學的一個轉捩點,你不認為如此嗎?至於你在2000年8月的被捕,現在看來是中國政府給獨立的中國文學的一份禮物。當然,那絕不是他們的本意!我非常高興成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榮譽會員……所以……我同意。」
1993年,《傾向》創辦初期,我向她討教,我曾將《傾向》的發刊詞英譯寄給她,告知她:「《傾向》雜誌不是一份純文學刊物,它的視野通過文學得以延伸;而經由其他話語形式,《傾向》將從更廣闊的視角觸及人的存在問題。」「《傾向》崇尚個人創作自由的至上原則和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傾向》雜誌秉持理想主義信念,儘管這種信念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遭歪曲和貶抑。它同時強調一種真正的知識分子精神,這種精神主要是指對社會和歷史變革的責任感與價值關懷。」她讀後,對這一發刊詞予以高度評價。
德孤,道孤,人亦孤。多年來,《傾向》的路一直走的很艱難。某些海外中國作家聲稱流亡文學刊物應該是「純文學的」。在背後指責《傾向》有政治背景,甚至處心積慮處地打壓《傾向》,在華人文化圈及美國詩人愛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70等《傾向》編輯顧問面前煞有介事地抵毀《傾向》,卻從不敢公之於眾,或公開論戰。我以《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新共和》、《紐約客》(New Yorker)、《巴黎評論》、《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柏林的《國際文學》(Letter Internationl)等歐美傑出文化刋物的刊發內容為例,為《傾向》的傾向辯護,我自問:「《紐約書評》、《紐約客》、《新共和》、《巴黎評論》、不介入美國或當今世界的政治嗎?《倫敦書評》、《國際文學》不介入歐洲或當今世界的政治和思想嗎?」
蘇珊完全認同,並稱那些聲稱一份流亡文學刊物應該是「純文學」的論調是自欺欺人,是怯懦文人逃避中國社會中文學、文化和思想現狀的自我催眠。我入獄後,她撰文伸張《傾向》的理念,為我和《傾向》辯護,她寫道:「是的,他在寫作,並且編輯了一份知識分子雜誌……1993年,他同一群和他一樣30多歲的中國流亡作家們創辦了一本叫做《傾向》的雜誌。這是一份季刊(迄今已出版十三期),在劍橋編輯(貝嶺和他的編輯同伴孟浪住在(波士頓)劍橋,在香港或臺灣印刷,兩千到三千本的印數,大多數由漢學家、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和作家訂閱;約一千多本帶進中國送發。……我不打算聲稱貝嶺沒有政治觀點。他當然有。他支持中國的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他極為熱衷於中國的獨立(或者“地下”)文化。我也不打算聲辯《傾向》是一個非政治的純文學刊物。貝嶺和雜誌上的那些作家們在民主政治和表達自由的問題上,從來不持中間立場。他們也刊登那些受到檢查的獨立中國作家的作品。他們翻譯和採訪了許多西方作家,包括謝默斯‧希尼、納丁‧葛蒂瑪71、切斯瓦夫‧米沃什72、奧克塔維爾‧帕斯73以及我本人、葛蒂瑪女士和我還是編輯顧問。中國和西方作家之間的對話是該雜誌的一個主要特色。……」74
她甚至細數《傾向》的內容:「對這本雜誌的涵蓋範圍給出一個大概的概念吧,1996年的《傾向》第7、8期合刊上刊登有約瑟夫‧布羅茨基的三篇短文和幾首詩的翻譯,一篇關於布羅茨基的評論文章,還有一篇文章是探討把布羅茨基的詩譯成中文時遇到的一些問題;關於宗教(儒家和基督教)在現代中國的一個專題;關於九十年代中國詩歌的一組評論;一個(高行健)劇本;還有幾篇文章是關於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海外中國女作家、德國知識分子對柏林牆倒塌的反應、以及『知識分子在一個封閉社會』的問題。這個封閉社會當然指的是今天的中國。」75
我愧對於她。
她對《傾向》的停刊表示極大的遺憾。她是傾向雜誌最盡職的編輯顧問,她幫助我選題,推薦好的作家及作品,她無償提供她作品的中文版權,她一直希望《傾向》可以復刊,甚至要為《傾向》籌款。可是,我在中國所受到的那致命的一擊,使我身心俱疲,同事們又天各一方,我決定讓刊物休刊。後來,當《傾向》轉型為出版社之後,我更力不從心了。
她將美國詩人寫給她的信轉給我,鼓勵我。要我用更多的心力寫出新的詩作。可是,我沒做到。
她一直期待著我把回憶錄寫出來,並答應要為我寫序或書評。可是,直至她去世,我始終沒能完成。
2002年,我獲選紐約公共圖書館年度駐館作家,她給我熱烈的祝賀。之前,她總是擔心我的經濟狀況,因為她不知道那些年我是怎麼活下來的,當她知道我獲得五萬美元獎金時,她鬆了口氣。這期間,我開始傾全力編輯哈維爾託付我的翻譯、出版他著作中文版的工作。我告訴蘇珊,這五萬美元獎金,可以創辦傾向出版社,可以出版一些我一直想出的書,臺灣和中國真正需要的書。她支持,但憂心我會血本無歸。
我不輕易去求她。但是,只要我有求於她,她總是百分之百地給予,從不吝嗇,幾乎是有求必應。
她當然傲慢,因為她不能忍受平庸。她傾聽,但她反應敏銳、犀利、咄咄逼人,善於修理那些自以為是者。我們交談時,只要她雄辯,滔滔不絕,我就傾聽。她好戰------好思想之戰。她直言不諱-----因為她不能容忍謊言和愚昧。她誨人不倦,她是長輩(有時,她對我說話的口吻像是母親在教誨孩子),有時,她確實挺凶的(因為我的不夠努力),不過,這沒什麼,我可以承受。
近幾年,她直面世局的時論犀利獨到,而且,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無可限量。每次我讀到她的文章,都一讀再讀、拍案擊節、難以放下,深被她的文字力量所震撼。久而久之,她授權我,可在第一時間將她在美國主要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立即譯成中文,在有影響力的中文媒體上同步發表,以尋求更廣大的影響力。
隨著當代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氛圍愈來愈惡劣,她的憂慮更加無盡,她更多地投入到對時代狀況的關懷和對國家黑暗的揭示中。我們的友誼,也從她對我的擔心轉化為我對她的擔憂,轉化為精神上的相互感應。
十
那是她一生中最具挑戰性的時期,也是,她最被世人關注的時期。她生命中最後的時期。
2001年9月11日,紐約和華盛頓遭到恐怖襲擊,兩座世界上最高的大廈成為灰燼,三千二百多人死亡。這一切,使得蘇珊憂時傷國,在注意力上有了完全的轉變。「九一一」發生時,她在德國,儘管作為一個美國人,一個紐約人,她哀痛不已。但她批評布希政府的中東政策,她在法蘭克福匯報(Messe Farnkfurt)及《紐約客》(New Yorker)上先後發表<強大幫不了我們的忙>(Unsere Starke wird uns nicht helfen)一文,文中評論劫持民航客機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星大廈的恐怖分子的一句話:「如果要說『勇氣』──唯一價值中性的品質,無論我們在別的方面怎樣評價那些兇手,我們不能指責他們是膽小鬼。」76,激怒了很多美國人。成為「九一一」之後,美團國內最異端的聲音,一時之間,成為美國民眾都在關注和談論的。據我所知,她很快回到紐約,前往紐約世貿中心廢墟,目睹現場後,她受到了更大的震撼。隨後,她對自已的觀點做了更為清晣的表述和澄清,甚至自我反省之前的言論。
2002年9月,911事件一周年之際,她和布希總統先後在紐約時報撰文, 她寫下〈真正的戰鬥與空洞的隱喻〉77一文,直諫布希總統的反恐姿態:「……當林肯這些偉大的演說被習慣性地援引或被套用於紀念活動時,它們就變得完全沒有意義。它們現在成為高貴的姿勢、偉大精神的姿勢。至於它們偉大的原因,則是不相干的。
這種借用雄辯造成的時代錯誤,在美國反智主義的大傳統中屢見不鮮。反智主義懷疑思想,懷疑文字。宣稱去年九月十一日的襲擊太可怖、太滅毀性、太痛苦、太悲慘,文字無法形容;宣稱文字不可能表達我們的哀傷和憤慨 —— 躲在這些騙人的話背後,我們的領導人便有了一個完美的藉口,用別人的文字來裝扮自己,這些文字現已空洞無物。」
她接著申明:「我不質疑我們確有一個邪惡、令人髮指的敵人,這敵人反對我最珍惜的東西 —— 包括民主、多元主義、世俗主義、性別平等、不蓄鬚的男子、跳舞(各種各樣)、裸露的衣服,嗯,還有玩樂。同樣地,我一刻也沒有質疑美國政府有義務保護其公民的生命。我質疑的是這種假戰爭的假宣言。這些必要的行動不應被稱為「戰爭」。沒有不終結的戰爭;卻有一個相信自己不能被挑戰的國家,宣稱要擴張權力。………美國絕對有權搜捕那些罪犯及其同謀。但是,這種決心不必是一場戰爭。……」
本著她一貫的信念,她沒有被震天動地的正義之聲所遮蔽,她追尋真相,追索事件的本質。甚至,在血癌「降臨」時,仍在《紐約時報雜誌》上發表了生前最後一篇長文〈旁觀他人受刑求〉78。這篇詳細剖析美國軍人在阿布格萊布監獄中對伊拉克戰俘施刑照片的繳文,論理充分,廣引博證。她審視暴力,解剖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 Rumsfeld)巧言令色地為惡行開脫的權力語言,全文既有蘇珊一貫的犀利風格、又充滿情感力度,論證著在這個影像泛濫的年代,記實照片仍具有著不可磨滅的道德震憾。長文最後,蘇珊的文字如鼓擊般充滿張力:「畢竟,我們在戰時。無休止的戰爭。戰爭是地獄,比把我們帶入這場墮落戰爭的任何人所預期的更可怕。在我們鏡子般的數字殿堂中,這些照片永不會消失。是的,一張照片似乎抵得上千言萬語。而且,即使我們的領導人選擇不去看它們,也會出現成千上萬更多的快照和錄影。不可阻擋。」79
直至生命的尾聲,蘇珊都在守護著,守護著「文字的良心」,正如她在耶路撒冷獎獲獎演說中的自白:「如果我必須在真相與正義之間做出選擇──當然,我不想選擇──我會選擇真相。」80
十一
她走得突然,生前未留下任何遺囑或遺願。按照她的獨子,傑出的散文作家(Essayist)大衛‧瑞夫(David Rieff)的決定,並經過巴黎市市長的特別批准。2005年1月18日,她71歲生日那一天,被安葬在巴黎蒙巴納斯(Patti Smith Montparnasse)公墓。墓碑上佈滿鮮花,親戚與友人們從世界各地趕來參加她的骨灰安葬儀式。她的墓與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沙特(Jean-Paul Sartre)、波娃、羅蘭‧巴特、貝克特等人的墓為鄰。巴黎,是她最後的歸宿。她的精神祖國。她──進入了那一長列已逝的偉大作家行列。
2005年3月30日,她生前常來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Judy and Arthur Zankel Hall / Carnegie Hall)為她舉辦了追悼音樂會,由她的友人,著名日裔鋼琴家內田光子81彈奏貝多芬的C小調第32號鋼琴奏鳴曲,弦樂小組演奏貝多芬和勛伯格的弦樂四重奏。蘇珊那張仰躺沉思的照片被投射在演奏大廳幕牆上。約三百位蘇珊生前的友人與文化界人士,一起參加了這場美國唯一的蘇珊‧桑塔格追悼音樂會。
終其一生,蘇珊無愧於她樹立的標準:「我一直認為書不是為出版而寫,而是必須寫才寫。而我的書應當一本比一本寫得好。這是一項自我懲罰的標準,但我一直對它信守如一。」82她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著作《旁觀他人之痛苦》83堪與她的經典著作《論攝影》相映成輝,全書不放一張照片,用純粹的文字闡釋照片下的戰爭暴戾,絲絲入扣地剖析紀實影像中的人類苦難。
1981年,蘇珊寫下另一篇重要長文〈寫作本身:論羅蘭‧巴特〉84。她指出:「羅蘭‧巴特所描繪的那種作家的自由,從局部上說就是逃逸。」她聯想到王爾德(Oscar Wilde)的內心獨白:「狂熱與漠不關心的奇妙混合……。」接著,她又談到了另外兩位與巴特、王爾德氣質完全不同的哲學家型作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沙特。她認為,尼采是「戲劇性的思想家,但不是戲劇的熱愛者」,因為尼采的作品中存在著一種嚴肅性和真誠的理想。而沙特要求作家接受一種戰鬥性的道德態度,或道德承諾,即作家的職責包含著一種倫理的律令。她甚至比較了羅蘭‧巴特和班雅明,她對他們兩人傾注了罕有的熱情,指出羅蘭‧巴特「沒有班雅明一類的悲劇意識,後者認為,文明的每一業績也是野蠻的業績。而班雅明的倫理重負乃是一種殉道精神……」85而羅蘭‧巴特和王爾德是另一類型,她稱羅蘭‧巴特和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是傳播遊戲觀,拒絕悲劇觀。
1997年,我就曾問她:『您在氣質上是更偏向羅蘭‧巴特呢?還是如您剖析的班雅明「一種深刻的憂鬱」式的性格類型呢?』
蘇珊沒有回答。
以我的理解,無疑,蘇珊熱愛羅蘭‧巴特,他們書信往來、相知相惜。但她對羅蘭‧巴特的一生作了深刻卻多少帶有保留的總結,她在讚美之餘,指出了唯美主義在文明衰忘時代的內在矛盾及不可能性。這多少與她對班雅明的分析不同。對班雅明,她似乎毫無保留地傾注著熱情,一種和談論巴特不同的熱情。是的,她在寫作上更多地實踐了巴特的美學和文學觀,甚至,超越羅蘭‧巴特,踏入了羅蘭‧巴特來不及進入的小說領域。但在氣質上,她卻完全屬於班雅明,即,對於我們的時代懷著深深的憂慮。
但她比班雅明更有鬥志,命更硬。她絕不言敗,即使死神降臨。
失去了她的世界,不僅貧乏,而且,將面對更多的邪惡。
作者簡介:貝嶺,詩人、評論家、文學編輯。2000年夏天,因出版文學刊物在北京入獄,在桑塔格、米沃什、鈞特‧葛拉斯、葛蒂瑪、亞瑟‧米勒與謝默斯‧希尼等國際作家營救下,由中美兩國政府協議,出獄赴美。
贝岭:在土星的光环下──纪念苏珊‧桑塔格(下)
(首发稿)
文章摘要: 直至生命的尾声,苏珊都在守护着,守护着「文字的良心」,正如她在耶路撒冷奖获奖演说中的自白:「如果我必须在真相与正义之间做出选择──当然,我不想选择──我会选择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