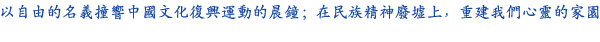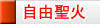三.
問:你曾經在演講〈中國的流亡文學〉*10中談到:「大部分的流亡作家,由於流亡中的適應和調整,生存的壓力,尤其是語言的不可逾越性,在文學上都失敗了,包括我自己。現在,我更像一個文學工作者,在寫作上已經不能和在中國大陸的心境、創造力、靈感相比了。」請問,如果這個時間無限延續的話,你怎樣自我認定?
答:不必掩飾。離開中國後,我的寫作,我的身心狀態,確實是一個流亡作家失敗的寫照。我的詩歌寫作漸少,甚至中止了。當然,我可以辯稱,我從來不是一個多產的詩人。對我來講,沒有什麼文字的勞作比寫詩更難的了。
尤其,當你的生存背景發生了從未料及的巨大變化,當時(1990年),一下子把我送進一所美國東部的長春藤盟校大學(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把我「扔」進英語系。我不僅是個(英語的)文盲,還是一個(英語的)啞巴,當時在布朗大學教書的台灣詩人楊澤曾目睹過我的窘況,他甚至被布朗大學校長請去為校長和我的面唔擔任翻譯。在沒有語言之前,你不是難民作家,你只是難民,你若沒有英語表達的能力,沒有人將你當真,你也無法弄假成真。
那些年我備受挫折,如同我在〈宿〉一詩中所述,是:
乞憐於語言,而又喪失了語言的日子
流亡中必要、非要面對的是「孤獨」。是大量以「孤」開頭的形容詞:孤獨、孤單、孤立、孤寂、孤零零、孤伶伶(自憐嗎?)、孤立無援、孤形吊影、孤掌難鳴、孤家寡人(假如你「不幸」單身、沒有家庭)、孤陋寡聞(那時還不是網絡時代)、孤魂野鬼(在外語的大原野)……它們變成了代替你的名詞,甚至成為如影隨形的動詞。你還不能被這「大原野」埋了(多少流亡作家埋沒了,母語丟了,又沒有真在這「大原野」上疾走)。在這「大原野」上,你還必須有些「孤高自許」(動詞意義上,甚至阿Q意義上的)。要孤注一擲,向內,也向外,坎坎坷坷、跌跌撞撞,視若無睹,即使「鼻青臉腫」,也要試著,在這外語的「大原野」上行走。
所以,我寫下了可以當悼詞讀的詩〈放逐〉:
我在時間的盡頭經歷放逐
手臂的彎度 記憶的弓
我用我的漢字洗清異國的天空
無倦的天空 遼闊強烈的天空
乾燥而又堅忍
帶著事物莫名的疼痛
冬天──有著記憶命名的莊重
我看到被遺忘拒絕的恥辱
帶著使命 進入我那野蠻的視野
眺望終止了閱讀 回憶放棄時鐘
經歷者──經歷著對經歷的厭惡
那並非是時間的過錯
那僅僅是時間的過錯
……
在後來的歲月中,我的工作重心轉為創辦並堅持辦下去傾向出版社,轉向相關的編輯工作。我的寫作,則轉向了散文(可以當「悼文」讀的散文)。
兩次的流亡,第一次(1989年,我選擇了留在美國,逾5年後,我又選擇回到祖國)和第二次(2000年秋,我被遣送出境,驅離中國),使我漸漸獲得完整的視野和對東西方世界的認知(這個西方世界至少有兩個部分構成,美國世界和歐洲世界),既使是在被資本主義全球化「催逼」的21世紀(這使我少了不少樂趣!),從細部看,你、我、他,民族、地域、人性、語言和文明的差異是多麼地不同啊。何況,我對伊斯蘭文明和伊斯蘭世界,對非洲黑人世界和非洲文化,對拉丁美洲世界和它古老的歷史和文明,甚至對東亞和日夲的文化和文明,又知道多少呢?
我第一次離開中國的那個年代(1980年代末)和我真正滯留美國的那個年代(1990年代初)是兩個如此不同的世界。而從1994年始,我一次次再返的中國又讓我多麼地感嘆不已。
暈眩和巨大的身心震撼。祖國慘痛的現實、祖國巨大變化的現實,對苟且偷生式流亡的自責,那扭曲的難民化美國生活經歷。在在,都寫在了我那不多的詩和更多的散文中。
問:就你自己的詩歌寫作而言,出國前與流亡後,有無語言和風格的變化?流亡使你獲得了什麼?失去了什麼?困境在何處?
答:和早年的詩作相比,我流亡中的詩在語境、意象、甚至風格上的變化顯而易見,可又有跡可尋。詩是需要破譯的日記,其實,在我1980年代的詩中,就有了預兆。
我從來不是一個每天坐在書桌前就能凝神疾書的人。我總要先從閱讀開始,有時,要持續很多天,然後,才能進入可能的寫作。可我對世界的變化有著太多的關注,對生命的美,對藝術、音樂、舞蹈、甚至時裝都充滿興趣。總有一些更有吸引力的事物或更迫切的事情將我帶離書桌,有時,我還會有些責任感,會憤怒、介入或自責,會以為有些使命要你去完成,而這常常不是寫書或寫詩。
我的困境何止一種,某些具體的還可以說出來,例如,病。例如,怎樣在寫作和編輯、出版這各不相同的工作中獲致平衛。怎樣在母語和非母語(英語)文化環境中少些顧此失彼,怎樣在我積習難返的單身生活中,尋求詩的心境和寫作的專心致志。
這兩年,我已漸少對流亡生涯的悔恨,開始認命(我認命了嗎?),並帶著距離審視祖國發生的一切。我已將流亡視為一種宿命,視為命運的一部份。
面對時間,流亡,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這些年,我有一些時日住在美國加州,以對比我已熟悉的美國東部文化和社會環境,我每年有三至四個月住在臺灣,以親近母語和母語文化,我也花更多的時間住在歐洲,以對美式文化、布希政治,對中國移民及海外「反對派」的政治和生活方式保持警覺和距離。
當然,我隨時準備著再次回到祖國。
享有獨來獨往的自由(就像我在歐洲的情形:省吃儉用,挎著布袋上路,踏自行車、迷路巴黎,在布拉格穿街走巷,在西班牙鄉村頂風、邁開大步,迎著乾燥晃眼的大太陽上山),繼續遷徙,跋涉,顛沛流離,走。讓流亡的不幸成為萬幸,不斷面對全新的人民、環境、文明和文化。
所以,既使我不置一詞,作為詩人,已經結束了嗎?,我對此質疑。
的確,我是一個文學工作者。而且,可能還是一個盡可能踐行相稱生活方式的文學工作者。在未來數年中,我的寫作和編輯工作不可怠慢。紐約公共圖書館學者和作家中心獎(2002—2003年)要完成的文學回憶錄,已在籌備中的作家訪談錄、一夲文論選,近十多年來詩手稿的整理成集、《傾向》編務文字的整理結集、這些都壓在案頭。
因為創辦《傾向》文學人文雜誌,使我涉入了出版,這些年,經歷了在北京因莽撞出版雜誌而入獄的劫難,也受夠了為書的出版「求爺爺告奶奶」的挫折屈辱,更因為,再也不想被動地等待中國不知何時「降臨」的出版自由。2003年,「流亡的」傾向出版社在台灣面世了,已策劃的「流亡年代叢書」鎖定翻譯出版有流亡經歷或作品曾經流亡的二十世紀重要詩人、作家和知識份子的著作,目前已出版了九夲,包括哈維爾的7夲譯著和索因卡的兩夲譯著。還出版了紀念之桑塔格的照片紀念集。接下來,還有哈維爾的照片傳記集、德語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的詩選和傳記、二十世紀波蘭最重要的詩人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詩選等。因為哈維爾的捷漢對照雙語詩選《反符碼》竟在美國的書店頗受歡迎。我甚至設定了一個目標,傾向出版社將陸續出版譯自不同語種的(包括雙語的)詩選。
既然人流亡,出版社流亡,索性,就讓書也在世上「流亡」吧。
自我的寫照或自我的忠告是:別無選擇。因為流亡,你將永遠成為一個邊緣人。你不可能將英語講得、寫得比母語還好。在所有的方面,你比所有土生土長的英語作家更為艱難,更沒有可能。你要比他們更勤奮,更珍惜時間,更多地工作。你還要學會不在移民社會的熱鬧中迷失,學會安貧樂道。少花時間在生計上。
小心,欲迎還拒,甚至能拒。要和體制和群體保持必要的距離,至少,要試著省視體制和群體給予你的虛榮和身份感,懷疑它。別讓誘人的體制遮蔽了你眺望世界的能力。
問:在你的那篇演講裏,你區分了作家與知識份子、文學工作者。你指的是特立獨行,對公共事務發言的知識份子嗎?
答:是的。真正的知識份子特立獨行,他對公共事務發言,不懼危險,發聲異議,揭露當政者和得勢者的偽善和謊言,並獲得廣大迴響。
當年捷克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主要異議者哈維爾就是榜樣,他甚至直接自我要求:「知識份子應該不斷使人不安……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反抗一切隱藏著的或公開的壓力和操縱,應該是體制和權力及其妖術的主要懷疑者,應該是他們謊言的見證人,一個知識份子應該不屬於任何地方,他不管在哪兒都應該成為一個刺激物,他不應該有固定的位置。」*11
同樣,我也一直記著「不用「知識份子」這個詞來描述自己」*12的桑塔格,在1997年就和我說過的話:「大多數知識份子和大多數人一樣,是隨大流的。在前蘇聯蘇維埃政權七十年的統治中,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是蘇維埃政權的支持者。或許最優秀的知識份子不是支持者,但那只是極少數。要不然怎麼會有作家協會、藝術家協會、音樂家協會之類的組織呢?甚至連帕斯捷爾納克(Pasternak)和蕭斯塔柯維奇(Shostakovich)都下過保證。在三十年代有多少俄國作家、畫家和藝術家受到殺害,一直到德國入侵俄國為止。當然,知識份子的歷史中也有英雄主義的傳統,這在現代獨裁統治下顯得更加光榮。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大多數藝術家、作家、教授——如果你用蘇聯的定義,那還得加上工程師、醫生及其他受過教育的專職人員——都是相當會隨大流的。」*13
她質疑我的一廂情願:「我覺得把知識份子和反對派活動劃等號,對知識份子來說是過獎了。在上一世紀和這一將結束的世紀,知識份子支持了種族主義、帝國主義、階級和性別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甚至就連他們所支持的可能被我們認為是進步的思想,在不同的情形下也會起本質的變化。讓我來舉一個例子。十九世紀,許多中歐和東歐的作家、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都在闡明民族主義理想的戰鬥中衝鋒陷陣。那些民族主義理想那時被看作是進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又比如,支持新的民族國家的產生代表了古老的團體和語言組織的利益,它通常伴之以對當政的專制集團及對審查制度的反抗。但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民族主義大多數表現為一種反動的、經常還是法西斯式的態度。所以,民族國家的理想含義隨著世界歷史進程的變化也起了變化。」*14
今天,直面社會、以筆為耕,不靠大學生存的波希米亞式知識份子已瀕於滅絕。我注意到,從自由的西方到專制的東方,大學都在無盡地擴張(當然,這對大學生們是種幸運),正在大量「收購」體制外的「名牌」作家和知識份子,包括帶有流亡背景的作家和知識份子,將他們馴化,成為喪失「野性」、品行「端正」、循規蹈矩、沉湎於校園或象牙塔內的生活、對外部世界一知半解,卻滿口術語的大學教授,而缺乏自信、也不願安貧樂道的作家和知識份子,則對大學教席趨之若鶩。
現在的中國,一個著述暢銷的作家、學者或知識份子,只要有知名度,又能在大眾傳媒上說些實話,就很容易被氾濫地歸稱為「公共知識份子」,一個在政治和個人自由上乏善可陳的國度,某個開明的官方媒體竟能在中國評選出50個「公共知識份子」,真不知該是悲還是喜?
影響力覆蓋國家、甚至超越國界的偉大知識份子,早如紀德、羅素、魯迅、羅曼‧羅蘭、愛因斯坦、阿多諾、漢娜‧阿倫特、薩特、波伏瓦、薩哈羅夫等,當代如索忍尼辛、桑塔格、薩依德、魯西迪、索因卡者,已經愈來愈少了。詩人、作家愈來愈像文字領域裏的專家(professional)、行家,而不是在公共視野中淵搏、發出尖銳的抗議、而且舉足輕重的偉大文人。
記得薩依德傳神地描述過流亡的知識份子,說他們「必然是反諷的、懷疑的、甚至不大正經-----但卻非犬懦的(cynical)。」*15他甚至將產生真正知識份子的希望寄託在流亡者身上。
四.
問:你曾經將1989後流亡的中國文學與流亡的中國作家與二戰開始後的猶太知識人流亡以及前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作家流亡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延續,但在今天,全球化、網絡時代,流亡作家發表的空間要比過去廣闊得多。「流亡」在網絡時代,是否還存在?
答:無疑,1989後流亡的中國作家和知識份子與二十世紀初俄國「十月革命」後部份俄羅斯作家、知識份子的流亡,和納粹時代猶太作家、知識份子的流亡,和二次大戰後前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制度下作家、知識份子的流亡以及暴政及宗教迫害下各國、各民族作家、知識份子的流亡是同一歷史境遇的延續。
二十世紀是充滿人類苦難、災難、戰爭、屠殺的世紀,是最大程度展現人性邪惡面的世紀,也是人類充滿原創力、技術、虛望和慾望的世紀。
從文學上看,二十世紀也是流亡文學輝煌的世紀。二十世紀世界性的流亡文學傳統中,有著可以共用的文化、精神資源。1989年後,流亡的中國文學應有以上的時空背景和精神特貭。
流亡,在地球村、全球化,在網絡時代仍舊存在,流亡是一種歷史刻痕,它可能被風化,卻無法抹去,只要暴政存在,只要對自由和尊嚴有著渴望,流亡就會存在。
流亡也是一種內心狀態,多少可以抵禦「窮人翻身」、成為新富人的世俗召喚。
確實,新世紀的流亡作家,比上一世紀大多數年頭的流亡作家要幸運多了。當代流亡作家的生存空間、視野,發表作品和表達見解的機會,比納粹主義時代,比冷戰時代要寬廣得多。
但是,地理上,他們和母國的距離並未縮短(儘管在心理上近得多了)。在精神上,他們可能被網絡時代的無距離假像所蒙蔽,以致於以閱讀代替一切,自外于祖國那活生生的現實,也和僑居國的文化、社會和文學環境相疏離。
二十世紀還是二十一世紀,冷戰前還是冷戰後,在什麼時代經歷流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流亡中你做了什麼和寫了什麼。
五.
問:你有幸成為蘇珊‧桑塔格和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友人,並與他們交往多年,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請談些感性的。
答:她和他都是對我的一生產生重大影響的人。
她(蘇珊‧桑塔格)甚至是直接改變了我人生的人。若不是她,我可能現在仍在獄中(半瘋,或者身心俱垮。)我不是那種可以把牢底坐穿,出來後又可以做大事的人。相對於民主(看人們煞有介事地掛在嘴邊上的),我更熱愛自由,愛到不可救藥。
她已故去(這是真的嗎?我常常有拿起電話撥給她的衝動)。我懷念她,時時想到她對我的鼓勵。
她和他(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個性完全不一樣。
桑塔格熱情中透著犀利,她目光犀利,思想更犀利,她是真正「堅定、獨立的個體靈魂」*16。她活得絕對精彩,是精彩,不只是多姿多釆。她的淵博,讓我想起文藝復興時代,想起啟蒙運動、想起狄德羅稱之為「百科全書」式的作家。和她交談,是思考、見解、理解力的高速遞進。她的睿智、心智,是天才才有的。
她不能忍受謊言和空話,她也不能忍受平庸和無知。
面對她,謙卑是無止境的。
哈維爾溫和和藹,和他相處時,你能感受到由然的溫暖,他會讓你把話講完,傾聽。他甚至帶些靦腆。可他一旦凝神思考,他的表達立刻犀利,表情也威嚴盡現。
她和他都有燦爛笑容的時刻。她隨即斂起,讓你回味。他卻不斷釋放,讓你難以忘懷。
她和他一生中都有許多時間在和死亡博鬥。可桑塔格從不讓你意識到她的病症,而哈維爾,卻時刻讓你意識到,他是一位病人。
桑塔格如嚴師、長輩,責我不夠努力,督促我。她擔憂我的安危、甚至助我生計。她也為我寫推薦信,介紹刊物發表我的作品。
哈維爾則如平和的友人,有時,和我扯些寫作的苦惱和作家間的軼事。
--完---
注釋:
*1孟浪〈必要的喪失︰1989後的中國流亡文學〉一文先後發表於2001年2月2日台灣《自由時報》自由副刊、同年3月4日美國《世界日報·世界週刊》、同年3月5日馬來西亞《南洋商報》和同年4月號香港《開放》月刊。
*2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1923-),南非小說家,反對南非種族隔离制度的自由鬥士。199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3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尼日利亞(奈及利亞)詩人、劇作家、小說家、評論家,
非洲民族的自由鬥士。由於「以廣闊的文化視野創作了富有詩意的人生戲劇」而獲得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非洲作家。
*4黃翔文〈流亡遊戲――質疑所謂“反對派”並對“異議者”持異議〉,原刊於2005年多維週刊。
*5貝嶺文〈筆會誕生始末〉,原以節選方式刊於2004年的《民主中國》網上雜誌,後以全文〈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創辦始未〉連載刊發於2007年的《自由聖火》網站。
*6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 1936-) ,捷克劇作家、思想家、異議分子,捷克前總統。
*7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美國小說家、文論家。近三十年來,她是具世界影響力的文人。
*8霍梅羅‧阿瑞底斯(Homero Aridjis),前國際筆會主席,墨西哥詩人。
*9薩爾曼‧魯西迪 (又譯為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 ,英籍印裔小說家,他的小說和言論影響力之大,竟招致伊朗宗教袖何梅尼下達全球追殺令。
*10貝嶺演講稿〈中國的流亡文學與地下文學〉,原為2003年秋天在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的演講,後紀錄成文。
*11原刊於哈維爾自傳《來自遠方的拷問》p177頁 ,傾向出版社2003年出版。
*12參見貝嶺、楊小濱1997年8月對蘇珊‧桑塔格的訪談〈文學.作家.人〉,原刊於《傾向文學人文雜誌》第十期(1998年)。後收錄於傾向2007年出版社出版,貝嶺等著的《在土星的光環下︰蘇珊‧桑塔格紀念文選》一書p222頁。
*13、參見蘇珊.桑塔格訪談錄〈文學.作家.人〉,原刊於《傾向文學人文雜誌》第十期(1998年)。後收錄於傾向2007年出版社出版,貝嶺等著的《在土星的光環下︰蘇珊‧桑塔格紀念文選》一書p225頁。
*14參見蘇珊.桑塔格訪談錄〈文學.作家.人〉,原刊於《傾向文學人文雜誌》第十期(1998年)。後收錄於傾向2007年出版社出版,貝嶺等著的《在土星的光環下︰蘇珊‧桑塔格紀念文選》一書p225頁。
*15、*16參見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知識份子論》,1997年麥田出版社中譯本,譯者單德興。
作者亦為美國加州大學(爾灣)翻譯和文學寫作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Writing & Transl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理事會執行理事

4, 貝嶺(2001年 9月)在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住處

5, 貝嶺(2005 年10 月15日) 在巴黎的ATELIER DE LA MAIN D'OR 音樂廳 朗頌誦詩